俺姥爷家族子嗣旺,他那一辈,亲兄弟堂兄弟数人,大都聚居在俺村后街一条小胡同附近。胡同口有一株大槐树,村里人称其家族为“大槐树底李家”。我母亲嫁在本村,闹得我打小一入后街,抬头所见,不是姥爷姥娘,就是舅舅姨。

大姥娘
大姥娘王氏,又高又瘦,瘦到贴骨,黄黄的脸,满头白发,人就像是风中的一根弯竹竿,风大了就能刮倒的模样。她家和我姥娘家在胡同口的一东一西,十步八步,就能从我姥娘家窜进大姥娘家。
大姥娘家有十个孩子,六女四男。姥娘说:大姥娘是猫托生的,吃叼零食,从来不上饭桌正儿八经吃饭。做好了饭,等待儿女们都吃完了,她依旧盘腿坐在炕上,守着烟笸箩,一捺长的旱烟袋,一会儿吧嗒两口,一会儿吧嗒两口。吸足了烟,下炕,趿拉着鞋,吃几口孩子们剩的残汤剩水,这就是一顿饭,然后再上炕盘腿坐下,继续吧嗒着烟。只要是去大姥娘家,十次有九次看她是盘腿弓腰在炕上吸烟。一看见我,就磕磕烟袋,细声慢语讲道:恁妈妈生你,六天,我去送鸡蛋。你那个脑袋,就这么大。她用双手拇指食指合起来,比了一个鹅蛋大小的圆圈,“不足月,七个半月生的你。比一只小猫大不了多少,也不睁眼,一只鞋就能把你装进去。我回来,跟你姥娘说,这孩子不能活。谁知道,还活了,还活了。”说到“还活了”这一句,她必定是拧上一袋旱烟,吧嗒几口。每次都是这一段,次数多了,我都能背下来了。
七八岁的我很调皮,再去大姥娘家,不等她磕磕烟袋开口,我就开始一本正经背诵了:恁妈妈生你,六天。我去送鸡蛋……大姥娘一口烟没憋住,呛得“吭哧吭哧”咳嗽,用烟袋锅指着我:这个小皮孩,这个小皮孩。我就一溜烟跑进里屋看三舅舅,留下姥娘和大姥娘在正房小声拉着闲篇。
三舅舅很帅,常年不见阳光的脸,煞白。姥娘私底下告诉过我,三舅舅是大姥娘四十五岁那年生的,打小是弱症,一年到头吃汤药,吃了好多年,水泼在沙滩上一般,不见好转。只是在风和日丽的春秋天,到门口的大槐树底下坐坐,其余时间都是躺在炕上,看书,听收音机。我站在炕边,摆弄三舅舅的一些书,三舅舅有时不动弹,就这么静静地看着我,有时伸出又细又长的白皙手指,握握我黑乎乎脏兮兮的小手,对我笑一下。
三舅舅二十七岁那年,走了。不到一百天,大姥娘也走了。那是个深秋的九月末,槐米已经老黄变硬,槐叶随风四处飘零。
二姥娘
大槐树罩着姥娘家和大姥娘家之间的胡同。胡同里四户人家,门朝东的是二姥娘、五姥娘家,门朝西的是三姥娘、四姥娘家。
二姥爷与原配生有一儿一女。原配病故,续娶马氏,是个逃荒要饭流落到我们村的寡妇,带着一儿一女,跟二姥爷又生了一儿一女。二姥爷家三窝孩子,三儿三女。姥娘家的后院墙是二姥娘家的前院墙。二姥爷整天喝得东倒西歪,不管家里的营生。后娘难当,穷家的后娘难上加难。二姥娘经常苦着个脸,搬个小板凳,木呆呆地坐在自家门楼子下。我从来没见她脸上有个笑模样,也很少见她到胡同口的大槐树下和妯娌们扯家长里短。姥娘带我去胡同里诸姥娘家串门,经常见她独自泥塑木雕般倚着街门,坐在街门口。二姥娘说的外乡话,我们听不懂,小时候不懂事,背地里管她叫“西府莱子老婆”。
春天,二姥娘在南墙根底种丝瓜。一到盛夏,丝瓜爬满了墙。我们海边人家,极少吃嫩丝瓜,只是用晒干的老丝瓜瓤刷盆刷碗,用丝瓜络做药引子。二姥娘摘嫩丝瓜,摘得了,隔墙喊我姥娘:大嫂子,分你几根炒炒吃。姥娘不相信嫩丝瓜好吃,又不好拂了二姥娘的美意,试着炒了一盘,打那才知道嫩丝瓜滋味很鲜甜。
二姥爷年轻时闯关东,染上了赖酒的毛病。亲戚本家,谁家请客,不请自到,一顿不喝,馋得难受。我小舅舅定亲是个大夏天,只是自家亲姊妹们聚一聚,预备了三四桌。半上午,二姥爷倒背着双手,歪歪倒倒进了街门。大舅舅一见,赶紧迎上去招呼:“二叔,喝点,喝点。”二姥爷也不客气,随着大舅舅的指引,坐在了小马扎上。大舅舅赶紧端上凉拌猪头肉、干炸鱼块,一瓶凌云大曲,三钱的小酒盅摆上。左一盅,右一盅,大舅陪着,不停地添酒夹菜,二姥爷一会儿功夫喝得双眼迷离,脸腮通红。姥娘出来道恼:“他二叔,别挑理,等你小侄子结婚,咱老李家不论长辈平辈,一家不拉,都请。”一边嘱咐大舅:“一会儿送二叔回家,酒和菜都给二叔带着,留着二叔晚上吃。”
入了冬,小舅舅要结婚,提前一个月,挨家去请族中长幼。姥娘站在后门口,望了望后墙上攀爬的凌乱丝瓜架子,叹息一声,对小舅舅言道:“这顿酒,你二叔是没赶上喝哇!”
三姥娘
三姥娘是个弃婴,从小养在育婴堂里。一岁多点,被本城徐姓大财主抱回家,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大财主夫妻俩年过五旬,无儿无女,对这个抱养回来的姑娘骄纵异常、百依百顺。徐家有绸缎庄、药铺、当铺,好多买卖,城西好几个村子里都有她家的土地佃户。二十岁之前的三姥娘,过的是呼奴使婢的阔小姐生活,横草不拿,竖草不动。吃得起参鲍燕翅,穿的是绫罗绸缎,一个肉丸的羊肉饺子都吃腻了。只要是上街,必定换一套时尚的新衣服不可。
听我姥娘说,未出嫁的三姥娘早年干过些反动的事,不得已才嫁给了赤贫如洗的三姥爷。二十年荣华富贵的大小姐生活,就像一场烟云,转眼即逝。嫁过来的三姥娘,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挤住在我姥娘家的三间小草房,一家一间半。直到五年之后,才在大姥娘家房后,盖起了三间房子。
三姥娘和我姥娘一样,三十出头,年纪轻轻就守了寡。我姥娘家两儿三女,三姥娘家一儿两女,年纪相仿,儿子和我小舅舅同岁,是个傻子。
姥娘和三姥娘走得最近。我最不爱跟姥娘去三姥娘家,去她家,我觉得阴得慌。我怕木桩子一样站在房地一动不动的傻舅舅。姥娘和三姥娘在屋里说话时,就会找点吃的,把我指使到院子里玩,不让我听她俩说话。三姥娘送我姥娘出街门,眼圈总是红的,一再说:大嫂子,你没事常过来坐坐。你过来坐坐,我心里能敞亮不少。姥娘一边答应,一边回头望望,傻舅舅还是一动不动,木桩子一样在房地站着。
我曾经看见姥娘在我妈妈面前为三姥娘掉眼泪,说她嫁了你三叔这个穷打渔的,没过一天舒心日子,要不是有个傻儿子牵绊,怕是早就寻了短见。
三姥娘晚年,因几十年的气郁忧闷,患了很重的糖尿病,“攻”在了眼睛上,双眼几乎看不见。糖尿病人最怕饿,青姨从生产队散工回来得晚,着急忙慌做饭。三姥娘着急吃,围着锅台打转转。又累又急的青姨怕她烫着,声音不免就大了点。一辈子不能被触尖的三姥娘,当晚就上了吊。
三姥娘出殡,青姨搂着姥娘嚎啕大哭:“大娘,俺妈妈这么走了,叫我这做闺女的可怎么活?可怎么活?”四姥娘、五姥娘一边一个,架着青姨的胳膊,也摁不住青姨满地打滚。
四姥娘
四姥娘高氏,十五岁被卖进了窑子。听姥娘讲,四姥娘用刀子攮死了老鸨子,夹个包袱逃出妓院,后被四姥爷收留。新中国成立后,妓院被政府镇压取缔,她才敢和老家通了联系。
四姥娘说话高音大嗓,声振屋瓦,穿着不修边幅,整天披头散发,人不怎么收拾,家也不怎么收拾。四姥娘有个姐姐,嫁在青岛。有一次我去她家,恰逢她刚从青岛回来不多日子,四姥娘开开大衣柜,抓出一大把软糖给我,是那软软糯糯、色泽浅黄、包着一层糯米纸的青岛高粱饴糖。
姥娘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就连蓬莱城一年都去不了三次两次。四姥娘眉飞色舞,讲栈桥,讲鲁迅公园,讲青岛有条中山路,中山路上有十几层的高楼,跑着拖着长尾巴的电车,还有个什么东西都能买到的“老婆孩子商店”,说得姥娘一愣一愣的。直到我二十多岁去青岛工作,在中山路上怎么也没找到四姥娘所说的“老婆孩子商店”,后来看到了“妇女儿童商店”的大招牌,想了一想,不禁哑然失笑,这一定就是四姥娘口中的“老婆孩子商店”。
四姥娘和四姥爷一辈子形影不离,只要看到高高瘦瘦的四姥爷,身边一定紧跟着又矮又胖、长成正方形的四姥娘。四姥娘一辈子没解怀,族中二三十个侄男侄女,他俩也不过继一个,两个人就这样清清净净、潇潇洒洒地过了一辈子。四姥娘去世不到半年,四姥爷也追随四姥娘于地下。
五姥娘
五姥娘阎氏,八岁父母双亡,用一根竹竿牵着瞎眼的爷爷沿街乞讨。十三岁那年,瞎眼爷爷死在了我们村的土地庙。李家老太太于心不忍,收留下这个讨饭的小姑娘。两年后,五姥娘十五岁,和五姥爷圆了房,生了五儿两女。姥娘经常跟我讲五姥娘当年牵着瞎爷爷沿街要饭的景况:十岁不到的小姑娘,面黄肌瘦,黄毛散乱,光着脚,没有鞋穿,怯生生敲开姥娘家的街门,声音像个小猫一样,小声哀求“大嫂子,可怜可怜,给口吃的吧”。姥娘转身进屋,拿着高粱面饼子、地瓜、咸菜疙瘩,递过去。转过身,免不了流下一串串眼泪。谁料想,几年后,施舍饭食的大嫂子竟真成了大嫂子,两人竟然成了妯娌。
姥娘家房子没翻盖前,是三间北屋,靠街有三间小南屋,都是破草房。五姥娘一家住三间小南屋,和姥娘家住一个院子,走一个街门,整整二十年。我母亲说她和五姥娘家的花姨同岁,两人放学一同拾草,一块剜菜,一起烧火做饭。隔着窄窄的天井,两个十多岁的毛丫头,一问一答:“你烧开锅了吗?”“俺家的锅冒气了。”“你做的什么饭?”“俺烀的饼子,熥的萝卜虾酱。”晚上,这两家十多个孩子,除了吃奶没下怀的,男孩赶在一铺炕上,女孩赶在一铺炕上,大的看着小的,一铺炕上仅有一床薄被子,连条褥子都没有,光身子滚在炕席上。
一直到五姥娘家的刚舅舅十八岁,五姥娘家才在二姥娘家房后盖了新房,搬了出去。我六岁那年,六月三伏天的大中午,天又闷又热,一丝风也没有,屋里热得睡不着,姥娘看着我在门口大槐树下玩,四舅五舅急匆匆从胡同里跑出来。姥娘问:老五,着急忙慌做什么去?五舅边跑边说:去大队找拖拉机,俺爸家里不好。拖拉机来了,停在胡同口大槐树下。四舅五舅抱着五姥爷上了拖拉机。拖拉机刚走不大一会儿,西北天上来了黑云,电闪雷鸣,瓢泼大雨夹杂着鸡蛋大小的雹子,打得瓦片噼里啪啦,大槐树的枝叶落了满地。雨住了,姥娘不放心,在大槐树下向东张望。傍晚,四舅五舅眼圈红红的,耷拉着头回来了。壮得像头牛一样的五姥爷,脑出血没抢救过来,撇下了还不到五十岁的五姥娘。四舅五舅还没成家,秋姨那年才十五六岁。
姥娘去世是阴历正月初五。那天,下了百年不遇的雪。没有风的暴雪下了一天两夜,平地积雪到大腿根。初六傍晚,四舅五舅搀着拄拐杖的五姥娘来辞灵。未进姥娘家的街门,大槐树下传来五姥娘粗哑的哭声。“大嫂子,我的大嫂子,以后我有个心里话,都没地方说了哇!我这从小要饭的——我是没有娘家的人啊!”
大槐树依旧枝叶繁茂,姥娘窝的姥爷姥娘们,一个个都不在了。九十五岁的五姥娘是大槐树下姥娘窝最后一个离世的。从小生活在大槐树下的舅舅姨们,掐指算来,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分散在村子的东南西北,足足有五六十户之多了。(李心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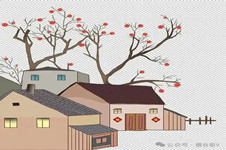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