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打开一直珍藏的父亲遗物:一本功劳证和一枚纪念章。睹物思人,父亲的音容笑貌浮现在眼前,缱绻在心底的思念,如潮水般涌来。轻轻地抚摸着红色的功劳证和闪着微光的纪念章,它们仿佛折射出父亲参加革命的那段峥嵘岁月,也蕴藏着贯穿他一生中的种种遗憾。

资料图 文图无关
一
父亲孙宝珍,1928年出生在烟台海阳东南的一个偏僻山村。他在兄妹中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和妹妹。早年间,家里虽然不富裕,但爷爷对自小就文静、聪慧的父亲寄以厚望,靠省吃俭用供他读了几年私塾,成为村里少有的读书人。父亲17岁时,爷爷又把他送到天津一家店铺做学徒,希望他日后能荣华富贵、光宗耀祖。父亲的哥哥,我的大伯早几年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父亲去天津的第二年也自己报名参军了,他的选择把爷爷气得捶胸顿足。
1946年,18岁的父亲怀揣着投身革命、建功立业的决心来到部队,希望参加战斗,消灭敌人。但因为那时部队里急需有文化的青年,父亲一直被留在后方做文职工作,虽然参加了淮海等战役,却没有真枪实弹地上过战场。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我的大伯跟随部队入朝作战,我父亲也给上级写了请战书,但并没能如愿。后来,父亲被部队送到军事院校学习培养了三年。
记得儿时,我跟随父亲到部队澡堂里洗澡,看到许多叔叔身上有可怕的疤痕,就问父亲。他告诉我,那是和敌人作战时留下的伤疤,当我好奇地问他,你身上怎么没有时,父亲表情复杂地叹了一口气没有回答。现在想起,我的问话也许戳到了父亲心中壮志未酬的痛点。翻开他的功劳证,里面仅记录了一次四等功,纪念章也是1952年颁发的一枚普通的慰问纪念章,并非军功章。
二
小时候,我眼里的父亲是英姿勃勃的,身穿着整洁的绿军装,帽子上的五角星闪闪发光。他淡眉细眼,总是笑眯眯的,加上国字脸上两片厚厚的嘴唇,更给人以憨厚、踏实的感觉。在我们家,母亲的性格直率,快言快语,也有些强势;父亲则性格温和,少言寡语,做事沉稳,对我们的管教也是言传身教,亦宽亦严。
那时,我们兄妹三个,属我最顽皮。麦黄时节,我和小伙伴们一旦发现大院里谁家的平房屋檐瓦下露出茅草,就找来梯子或顺大树爬上房,掏麻雀窝。有邻居来找父母告状,说我掏鸟窝把他们家的房瓦踩碎造成漏雨了。这时,父亲赶紧上前给邻居赔不是,母亲则一边训斥着我,一边发狠地对父亲说:“这孩子得好好管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父亲则笑呵呵地说:“咱家出了个调皮捣蛋的,将来可能有大出息哩。”事后,父亲悄悄给了我两元钱说:“喜欢鸟,就去买只好的养着,别去掏麻雀了,太危险!”
父亲对我是宠爱的,也是严厉的。有一次,小伙伴易卫东的父亲出差时给他带回来几只彩色玻璃球。弹玻璃球是那时我们最爱玩的游戏之一,不过玩过的玻璃球经过摩擦、碰撞表面会粗糙不堪。易卫东的新玻璃球透明闪亮,里面还有红的、黄的花瓣,滚动起来色彩缤纷。我不由起了贪心,欺负他比我小,就半耍赖半抢夺地将新玻璃球全部收入我的囊中。那天,易卫东是哭着回家的。父亲知道后找到我,收起脸上的笑容说:“你喜欢的东西,可以用正常的输赢来获取,但绝不能用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目的!”我知道错了,就找到易卫东,把玻璃球全都还给了他。
三
“文革”后期,在军区司令部担任参谋的父亲被派往省公安厅担任军代表。工作结束后,厅领导与父亲商量,想留他在厅里工作,被深爱部队的父亲婉言谢绝了。回到军区机关后,父亲向上级请求去基层部队锻炼。1974年,我们全家带着仅有的两只行李箱和被褥等全部家当,蜷缩在一辆解放牌卡车的车厢里,从省城济南一路颠簸地来到黄海前哨——荣成县的石岛。
父亲来到石岛守备团,属平级调动,担任了副团长。但他毫无怨言,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一天深夜,父亲接到报告,急匆匆地出了家门,一连几天没有回家,据说是苏山岛防区发现了敌情。那时,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早些年在镆铘岛就发生过敌特趁夜深企图登陆,结果被战士和民兵迎头痛击、仓皇逃离的事件。
正当父亲意气风发、干劲十足的时候,1975年的大裁军开始了。父亲的名字出乎意料地出现在第一批转业干部的名单里,他那时才40多岁,团里也有比他岁数大仍留下的。有同事劝解道:“你刚来,对各方面的情况还不熟悉,只能是你先走了。”那段时间,父亲在屋里一圈一圈地踱着步,显得有些郁闷。
父亲转业后,被分配到烟台的一家交通部直属单位。起初,因为单位要在荣成建立一个工作站,父亲就负责建站的工作。我1977年高中毕业时,想去参军,父亲没同意,他对我说:“你哥当兵了,你就进工厂吧。学个技术,将来凭本事吃饭!”他还亲自去县劳动局,给我选定了去汽车运输公司干汽车修理工。1978年工作站建成后,全家人除我之外都回烟台了。
多年后,我曾对父亲抱怨:“你那时如果去了公安厅或者让我当兵,我现在肯定不会是大集体企业的身份,不会进不了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父亲听了,表情平淡地说:“学好技术,比什么都强!”
四
1983年,我调回烟台,与家人团聚了。1984年结婚前,单位在市区分给我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父亲带着哥嫂将房屋粉刷、布置一新后,还托人买了一个能做饭可取暖的两用蜂窝煤炉子在屋内安上。
难忘1985年末那个寒冷沉闷的早晨,天还没亮,我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我睡眼惺忪地打开门,只见父亲一脸疲惫地站在门外,他对我说:“昨晚的气压低,炉子容易倒烟。我们单位的高压氧舱今早收治了几个煤气中毒的。我担心你屋里的炉子,过来看看。”我赶忙让父亲进屋,他摇摇头说:“不了,回去还要上班。”他又轻声嘱咐我:“你对象快要生了,要好好照顾她啊!”说完转身走下楼去。我望着父亲瘦弱的背影,心头一热,眼睛湿润了。这么冷的天,他从十几公里外的芝罘岛骑自行车赶过来,谈何容易。他的岁数大了,还患有高血压等疾病,依然时刻惦念着我们。没想到,父亲与我的这次见面,竟然成为我们最后的谈话。
不久后的一个夜里,哥哥急匆匆地来找我,说父亲住院了。我们赶到医院时,只见父亲表情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仿佛是累极熟睡似地打着鼾声。母亲哭诉着父亲发病的过程:当天父亲下班回到家,告诉母亲单位通知了,他可以回家退养了。母亲听了挺高兴,晚饭包了水饺。吃饭时,父亲一反常态地话多,一会儿说希望儿媳能生个胖小子,一会儿憧憬着以后的休闲生活,说着说着突然停了下来,冲母亲喊头痛,接着就不省人事了。
医生诊断后,说我父亲是脑溢血,没救了。当时,我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更不愿相信医生的话。可是,第二天中午,父亲的鼾声忽然停止了,随后如释重负似地长叹一口气,就没有任何声息了。刹那间,我觉得眼前一阵眩晕,不由得双膝跪下,紧紧地搂着父亲恸哭起来。
父亲去世三个月后,我的儿子降临人间。我不禁悲喜交加,喜的是自己有儿子了,悲的是父亲没有等到这一天。虽说人世间总会有生离死别,但如此的“擦肩而过”和倏然离去,使我倍感人生的变幻莫测和“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彻骨悲凉。
父亲他生活简朴,几乎没有什么嗜好,平时烟、酒、茶一样也不沾,但这并没有让他健康长寿,去世时才57岁。他甚至没有留下一句话,没有享受过一天的退休时光,更没能看到心心念念的孙子,过上含饴弄孙的幸福生活。
父亲的一生平平淡淡,在生活和工作中,有幸福和喜悦,也有许多憾事,但这并不代表着失败。从父亲身上,我学会了对待工作要勤勤恳恳,对待同事要谦虚和善,对待家人要充满关爱。我想,父亲在遥远的天堂如果能看到,他曾经的同事、朋友,经常来看望我母亲并嘘寒问暖,有一位叫扬夕岳的叔叔还时常送钱送物;如果能看到,现在我们兄妹都已相继退休,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如果能看到,他的孙子考上了国外的名校,工学硕士毕业后进了企业搞技术,真正实现了他“凭本事吃饭”的抱负……他的脸上一定会露出欣慰的笑。(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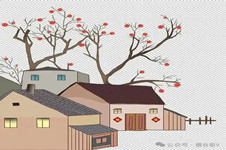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