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看月亮。总觉得那清冷的月光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磨着记忆,直到心里渗出血来。
母亲病重那年,家里总是弥漫着中药的苦涩味道。每到黄昏,那只粗陶药罐就蹲在灶上,火苗舔着罐底,药汁咕嘟咕嘟地翻滚。我坐在她身旁的小板凳上,看着月光从窗户透进来,落在她的白发上,像覆了一层薄霜。

“这药苦不苦?”我问。
母亲摇摇头,用竹筷搅了搅汤药:“不苦,像凉茶。”
可我知道,苦。有一次母亲喝了一半,皱着眉放下碗。我偷偷尝了一口,苦得舌根发麻。母亲最终还是喝完了,一滴不剩。月光下,她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像一根弯折的芦苇。我明白,她咽下了苦药,却把甜意留在哄我的话语里,只是怕我担心。
儿时的冬夜冷得刺骨,母亲说被子晒过就暖和了。她挑阳光最好的日子,把棉被抱到院子里,挂在晾衣绳上拍打。傍晚收回来时,被子蓬松得像云朵,带着太阳的味道。遇到阴天,她就换一种法子——把被子叠好,放在窗前,等月亮出来晾一晾。“月亮也能晒被子?”我不信。
母亲只是笑笑,说:“你试试就知道了。”
钻进被窝时,竟真的觉得暖和,只道是月光烘暖了棉絮。后来才知道,是母亲悄悄把用自己的体温焐热的被子盖在了我身上。
母亲最后一次住院,我陪夜。病房的窗帘没拉严,月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她的枕头上。她睡得不安稳,眉头微蹙,白发散在枕头上,像一蓬凋萎的芦花。我伸手想替她拢一拢头发,却摸到一把干枯的发丝——它们不知何时已变得如此脆弱,轻轻一碰就脱落了。我慌忙缩回手,仿佛触到了一碰就碎的月光。
我忽然觉得月光太亮,刺得我眼眶发酸。
“几点了?”母亲迷迷糊糊地问,声音轻得像飘落的羽毛。我告诉她是凌晨三点,她“嗯”了一声,又闭上眼睛,喃喃道:“你快睡吧,明天还要上班。”那一刻,月光像水一样漫过病房,她的轮廓在月光里渐渐淡去,仿佛融进了白色的床单。
母亲走后,我总梦见她在月光下忙碌的样子。有时是她借着月光纳鞋底,有时是她趁着月色干农活儿,有时她什么都不做,只是站在月光里,静静地等着我……我想喊她,却发不出声音。
收拾母亲的遗物时,在抽屉深处找到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四月十八夜,有月亮,西沟浇小麦,掐点麦穗给娃蒸青麦仁儿吃……”“八月十五夜,大月亮,正好摘花生,也不知道娃在学校吃月饼没有……”“冬月初九,半夜榨完花生油,趁着月亮推回家,明天给娃捎去一桶……”我怔怔地看着,眼泪砸在纸上,洇开了墨迹。
前些天,我又梦见了母亲。
醒来时,窗外月色正浓。我望着那条从家门口延伸出去的小路——母亲生前常站在那里,身影被月光拉得细长,像一根等我的芦苇。如今路上空荡荡的,只有月光铺了满地,像她给过我的爱,碎碎的,亮亮的。我蹲下身,一片一片去拾,却怎么也拾不完。(刘志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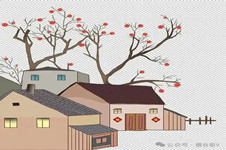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