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6年,故乡那些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往昔只能租种土地的佃农们就此翻身,成为土地真正的主人,彻底告别了流浪街头、栖身于破草房的困苦生活。
我的故乡是一个仅有三十户人家的袖珍小村落。村民大多是在讨饭途中于此聚集,靠着给地主打长工、做短工维持生计,逐渐沦为租地耕种的佃农。村里的房屋与土地被全面清算、合理分割后,一户户贫穷的佃户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耕地和安身之所,我家就是其中之一。

我家幸运地分到了4间小瓦房,其中一间用作过道。过道供三家住户日常通行,属于共用区域,过道上方的阁楼划归我家所有。这样算下来,我家的实际居住面积达到了37.12平方米。这对于深陷困境的我家来说,宛如黑暗中陡然透进一束耀眼的光芒,成为我们生存下去的希望与坚实的底气。
之前,村里除了地主家的大瓦房、小瓦屋,穷人家住的都是自行搭建的草房、半土半草房。破旧的土坯院墙摇摇欲坠,斑驳陆离的墙壁尽显凄凉。村子里的小路被野草肆意覆盖,整个村子弥漫着荒芜破败的气息,处处都是沧桑岁月刻下的痕迹。
曾经,我们一家在摇摇欲坠的半土半草房里艰难求生。分到小瓦房不久,那间破旧的草房便在风雨的肆虐下轰然倒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有了遮风挡雨的安身之所,有了生活的希望,父母整日将党的恩情挂在嘴边。
二
分到房屋的同时,我们家还在村西山半腰处分得了一块约三亩的土地。这块土地大部分种着果树,小部分可用来种杂粮。这片果木园历经岁月侵蚀,我们接手时已杂草丛生,一片荒芜。不少苹果树腐朽枯死,树干被虫子蛀得千疮百孔,蚂蚁在其中筑巢安家,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头。
有了养家糊口的土地,父母满心欢喜,每日早出晚归,不辞辛劳地在果园里默默劳作。当时,修剪果树的技术人才极度稀缺,苹果不仅结果少,还常遭虫子啃食,土地收益十分微薄。即便如此,父亲依然下定决心要让这片土地重焕生机。他如饥似渴地刻苦钻研果业知识,终于学会了果树嫁接技术,将老苹果树全部嫁接上新品种,又精心栽种了新树苗。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果园终于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为了更悉心地照料果园,父母在园子里盖了一间小房子。建房的过程艰辛异常,每一块石头都是他们从河套里,一步一步艰难地扛上山的。那些沉重的石头,饱含父母辛勤的汗水,见证着他们创造生存奇迹的坚定决心。屋顶的小灰瓦,是父母多年省吃俭用,一分一毫攒钱买来的;房子的梁和柱,则取自山林中的柞木树干。
小房子被巧妙地隔成两间,里间垒了个小巧的土炕,炕面铺着父亲从村旁山沟捡来的青石板——那原是有钱人家丢弃之物。这个虽然很小却很实用的土炕,能睡下两个人,白天可用来做饭,晚上炕热后,父母常常靠着它舒缓劳作一天后疲惫的腰腿。土炕旁还能放下一张小桌子,用来放置暖瓶、水杯等日常用品。中间的隔断墙上,专门设计了一个用来放置煤油灯的小窗窝,灯光能同时照亮里外两间屋子,这传统而巧妙的设计,处处彰显着老一辈人的生活智慧。里间南墙上开了个小窗户,糊上白纸后,屋内顿时明亮了许多。
外间垒着小巧的锅灶,一日三餐,母亲就在这里煮着地瓜干。偶尔改善生活,会在锅边贴上苞米饼子,锅叉上用碗蒸几条小咸鱼。下雨天无法劳作时,父亲就会烧火做饭,烤些小咸鱼、地瓜、苞米,再喝上几口自己亲手酿的大梨酒,惬意地哼着小曲,一家人其乐融融,欢声笑语在小屋里回荡。锅灶东南角,放置着一个小橱柜,用来存放餐具。这十多平方米的小房子,每一寸空间都被我们精打细算地充分利用起来。
三
正所谓“有钱有有钱的过法,没钱有没钱的活法”。父母穷怕了,常念叨:“只要有口吃的,能填饱肚子,就知足了。”我家房子后面有一棵杏树,每到果实成熟时,沉甸甸的累累硕果压弯了枝头。那是一种名为蛤蟆杏的品种,站在后窗户边便能轻松摘到。每年卖杏子的收入20多元钱,为家里增添了一笔颇为可观的收入。在小房子东南约六十米处的低洼山谷,父亲费尽心力挖了一个两米多深的大坑,用石头精心砌好四周,再盖上木板,这便成了我们家日常取水的水井。
1958年,土地、果木园被统一收归集体所有。父母毫无怨言,将这片倾注了他们无数心血的土地,郑重地交给了人民公社。
我的家乡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灵水秀,如今已经拔地而起许多高楼大厦,曾经泥泞狭窄的小道,化作宽敞整洁的水泥街道,道路两旁绿树成荫、花草繁茂,已然成为老百姓宜居的风水宝地。
岁月悠悠,记忆沉淀。那座承载着家族历史的家宅,至今依然静静矗立着,虽已略显陈旧,但一砖一瓦、一窗一炕、一锅一灶,仿佛娓娓讲述着过往的故事,承载着独特的历史,让人既倍感亲切,又觉新奇,俨然成为见证我们家族历史的珍贵“文物”。(陈世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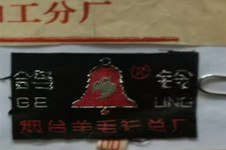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