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95岁的姨姥爷和91岁的姨姥姥是一对公认的神仙眷侣。姨姥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军的离休老干部,当过警卫员,看押过劳改犯。或许与不凡的经历有关,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不怒自威。可在娇小玲珑的姨姥姥面前,他宁愿卸掉所有盔甲。
姨姥爷的名字很励志——孙振荣,自小父母双亡,13岁开始到地主家当长工。1949年5月,部队到村里征兵,17岁的姨姥爷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军营。他忠厚纯朴,吃苦耐劳,第二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自豪与感恩成为姨姥爷的人生信条。
因为离得远,我见姨姥爷的次数很少,印象却特别深刻。第一次看见他时,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根本不知道他的职业和经历,只是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捕捉到一种特殊的军人气质。当时,姨姥爷是一名公安干警。
在公安局工作的姨姥爷总是很忙,姨姥姥独自带着孩子们在乡下老家生活,一家人只有节假日才能团聚。依照姨姥爷的资历,有好几次给家属、孩子办理农转非和安排工作的机会,他却一次又一次地让给了别人。
二
离休之后回到老家,姨姥爷仍如赛道上的运动员,难以停下奔忙的脚步。他要找事儿做,于是,一位修路的老人时常独自出现在山村的街道上。姨姥姥只要看见老伴儿提着筐扛起铁锨往外走,就知道他这是又遇见“路不平”的地方了。他怕走夜路的人摔倒,怕老人和小孩不小心崴了脚,唯独忘记了自己年事已高。姨姥爷提着一筐一筐土将路上的坑洼处一一填平、踩实,心才踏实。他顶着一头汗水心满意足回到家,姨姥姥急忙取来毛巾,踮起脚尖一边替他擦汗,一边心疼地虎着脸埋怨他。姨姥爷也不分辩,像个大孩子似地低下头乖乖地站着,任凭姨姥姥手里的毛巾在他脸上游走,心里如食甘饴。忽然他发现,这个娇小美丽的女人,如今已经成了头发花白的小老太太,曾经光洁的额头爬上了皱纹。姨姥爷鼻子一酸,几滴浑浊的眼泪洇入姨姥姥为他擦汗的白毛巾。
冬日,雪后山村清晨的第一串脚印是姨姥爷踩出来的。人们在睡梦中听见“刷刷刷”的扫雪声,从家门口一直扫到大街上,扫出孩子们的上学路。有人不解地嘀咕:这老头儿是不是脑子坏了?姨姥爷只管低头扫雪,胡茬儿上结了细细碎碎的冰凌子。姨姥姥担心他老胳膊老腿的摔倒吃大亏,严厉制止他扫雪,他只是呵呵地笑着。姨姥姥看着他胡茬儿上慢慢融化的冰碴儿,笑着笑着眼角就溢出了泪。姨姥姥知道,她说的每句话姨姥爷都无条件服从,但修路和扫雪例外。

姨姥爷耳背,听不见别人的闲言碎语,却听得清老伴亲切的唠叨。其实,对姨姥爷来说这不是唠叨,是被爱浸泡了几十年的佳酿,喝习惯了也会上瘾。姨姥爷说:“人老啦,干不了什么大事,只能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情。要对得起每个月国家发的养老金,对得起曾经穿的那身军装。”其实,老两口心里都明白,如今衣食住行这么好,哪一样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
姨姥姥一辈子掌管家里的经济大权,姨姥爷乐得当甩手掌柜。月底,姨姥姥背起挎包从储蓄所取来工资,姨姥爷眯着眼睛,坐在门前的核桃树下打瞌睡。树上挂着的鸟笼里,一只八哥正欢快地跳舞。姨姥姥轻轻将老伴儿摇醒,拨开那一树的蝉鸣,凑到他耳边大声说:“又涨工资啦,等赶集给你买把新扫帚,今年冬天你得继续扫雪呢。”八哥也来凑热闹:“扫雪、扫雪。”一口地道的黄县腔。
姨姥爷眯起眼睛笑。
三
姨姥爷喜欢摆弄小菜园。最初,是他主动邀我和妹妹去后院看他种的菜和花,后来我每次去,都嚷着去后院看他种的菜和花。那里有一簇一簇姹紫嫣红的四季花,在阳光里朝我眨眼睛;水灵灵的蔬菜泛着绿油油的光,菜畦子整齐得像方队。一条黑狗卧在老柿树下,瞪着一双黑亮的眼睛上下打量我们。黑狗不吠,喉咙里呼噜噜地响,像是努力隐藏着对我们的敌意,尽量在主人领来的客人面前表现得儒雅一些。有次去,不见了黑狗,只有几只黑的白的小狗娃在脚边蠕动。原来,黑狗生下几只狗娃以后突然死了。它是陪伴了姨姥爷多年的老朋友,姨姥爷特别悲伤,悄悄哭过,失眠过。几天后,细心的女儿发现老爷子的腿发软打颤,才知道他把自己每天早晨的那份牛奶偷偷分给没娘的狗娃们喝了。
姨姥姥家墙上挂着镶玻璃的相片框,一帧一帧照片仿佛时光机,还原着老两口从黑白到彩色的70年光阴。年轻时的姨姥爷一脸严肃,即便有秀气美丽的姨姥姥幸福地依偎在身边,他也不肯将倔强的嘴角上扬。老年的姨姥爷面相温和了许多,完全是个慈祥的老人家。一张姨姥爷胸前挂满各种奖章的单身照极为醒目,他没提过自己一生的任何功绩,只有那些闪亮的奖章替他记录着。
姨姥爷床头挂着16句的《长寿诀》,每天早晨背一遍,一气呵成。他坚持健身,能双腿并拢,双手交叉触到脚面。
姨姥爷家门前的老核桃树根深叶茂,一穗一穗的核桃花在暗暗结果。鸟笼和八哥不见了,姨姥爷咧嘴笑:“给孙女啦。”
姨姥爷95岁大寿,饭店开车送来一桌菜肴,一碟一碟往家送。姨姥姥在院里大声喊:“来家吃饭喽——”(魏青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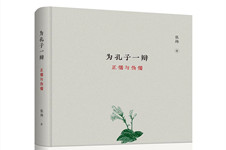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