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到夏天,我就要去山上拔山姜,和着艾蒿拧成蒿绳用来熏蚊子。
山姜的学名叫地椒,又名百里香,是多年生类灌木状草本植物。地椒喜欢阳光和干燥的环境,多生于向阳的山坡地,一簇簇火柴棍粗细的枝茎约二三十厘米长,长满密密麻麻的小叶子,顶端开着一朵朵淡紫色的小花,散发着幽幽的清香。在疏松沙质土壤且排水良好的山坡上,一片连着一片。

山姜资料图
那时候的农村,三伏天的夜晚最难熬。天气热得透不过气来,蚊子嗡嗡地叫着直往身上扑。
不光没有风扇、空调,有蚊帐的人家也是屈指可数。家家户户都是大铁锅连着大火炕,一天三顿烧火做饭,屋子里就跟蒸笼似的。每天吃完晚饭,男女老少都带着麻袋皮或草帘,到空旷的村路边、打麦场或河滩上乘凉。一直清凉到半夜,感觉夜里要降温了,才回屋里睡觉。
家里的老人会提前把蒿绳点燃,用一根长木棍悬挑着,插在橱柜的抽屉里,浓浓的艾草香味就在屋里弥漫开来。蚊子被熏跑了,一家人才能睡着觉。一个夏天,如果没有蒿绳陪伴,实在是没法熬过去。
我爹爹去世得早,母亲和几个还未成年的哥哥都在生产队挣工分,到了年底我家还是欠钱户。我和姐姐都是念了一年书就退学了,整天到山上挖野菜、拾柴禾、拔山姜。
从我们村翻过南面山梁有个村子叫后庄。我11岁那年,后庄村进了一套榨山姜油的设备,在周边村子贴出了收购山姜的广告,每斤山姜8分钱。像我们这样贫困的家庭,听说山姜能卖现钱,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就让我和姐姐专门拔山姜卖钱。
姐姐比我大一岁,每天吃完早饭,我们两个就各自挽着一个大柴篓子,到离村3公里远的东山上去拔山姜。那里有一片山坡叫“磨老刀”,因村里的磨刀石都出自那里而得名。那一大片山坡全都是风化的碎石,松散散的,根本长不出树木,也没有杂草,只有山姜耐得住干旱和贫瘠的土地,贴着地皮爬着生长,无论多少天不下雨,它们也能顽强地生存下来。
到了那里,我们顾不得歇息,就麻溜溜地蹲下,动手了。虽然我俩年纪小,可从小就干这些营生,一点也不打怵,两只手一刻也不闲着,一把一把拔起来放进篓子里。如果手被石头碰破了,就找个“灰包窝(马勃)”敷在伤口上,一会就能止血。半晌午的工夫就能拔半篓子,肚子也“咕咕”叫了,姐姐招呼我歇口气吃点东西充充饥。
说起吃的东西,其实就是找几个长在石缝的“老娘们脚丫子”,那模样就像现在家庭盆栽的“多肉”,吃到嘴里有一股酸溜溜的味道。不过,吃上两个还真能让肚子抵挡一阵子。
篓子装满了,姐姐就站在孤石顶上,看到村里屋顶冒出了炊烟,我们就开始往家里走。一篓子山姜也就是十斤左右的重量,可一个刚刚十岁出头的女孩背着一篓子山姜从崎岖的山路上走下来可不容易。走一会儿歇一歇,等到家时,两条胳膊都压出了深深的红印。
找个空旷地儿,把山姜摊开晾晒。由于它的枝茎本来就干巴巴的,一天的工夫就晒干了。妈妈就让我俩每天上午去拔山姜,下午把山姜抬到后庄去卖。
从我们村到后庄虽然也就是几里路,可中间隔着一道陡峭的山梁。我和姐姐把山姜结结实实地装在草包里,用绳子捆紧包口,穿一根长木棍,抬着就上路了。姐姐长得比我略高一点,每次都是她在后边我在前边。由于山路陡峭,上坡时后面的重量大,姐姐走起来很吃力,下坡时重量又到了前面的我这里,就很是吃不消。一个不小心脚下一滑,我们两个人就会随着草包摔倒。每当这时,我俩就互相埋怨,一路上吵闹不休。
记得那一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是家家户户烙巧果的日子。天太热了,等我俩抬着草包翻过山顶,浑身大汗直流,连头发都湿透了,真有点受不了。就在这个当口,我脚下一滑摔倒了,右腿的膝盖被石头碰破了一大块皮,鲜血直流。又热又累又痛,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干,转过身要往家走。姐姐一看急了眼,她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山姜背到收购点,就用好话哄我。我非要回家,姐姐把我按在地上,狠狠地打了几巴掌。我看她急得红了眼珠子,打心底里害怕,只好爬起来,流着泪把山姜抬到了收购点。
到了山姜收购点,那里的负责人就用木杆秤为我们称好重量,大声数着把钱递到我们手里。为了这几毛钱,妈妈特意在姐姐的衣襟上缝了个小布袋,姐姐总是小心翼翼地把钱装进去,一路上时不时摸一摸,生怕弄丢了。
后庄村那个山姜榨油点干了三年就收摊了。那几年的夏天里,我和姐姐就这样重复着拔山姜和卖山姜,那弯弯曲曲陡峭的山路上,留下了我们深深浅浅的脚印。日子虽然很苦,我们还是在不知不觉间长大了。抬着山姜爬那道山梁,“叽叽歪歪”的吵闹声少了,多了些不成音调的歌声。
还有,姐姐打我那件事,当天回家我就和妈妈说了,妈妈什么也没说,做饭时偷偷煮了两个鸡蛋给我俩,就算把这事摆平了。(华枝/口述 刘甲凡/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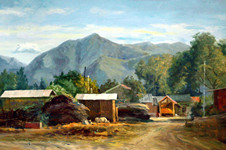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