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和本家兄弟孙乃强前往牟平博物馆办事,把导航目的地设定于雷神庙。驱车将近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减速慢行,沿着牟平区东南部的雷神庙大街寻找。走到大街东头,道路北边就是雷神庙。雷神庙坐北朝南,四合院,占地看上去不足五亩地的光景。门口东边十几米处,有一个卧碑,上书九个鎏金大字:胶东抗日第一枪遗址。大门上方,红底匾额上写着“胶东抗日第一枪纪念馆”十个金色大字。
小时候,“雷神庙”这个名字就如雷贯耳,一是因为青史留名的“雷神庙战斗”发生在这里;二是我村的张德惠烈士,就是在这场战斗中英勇牺牲的。

我俩静默地站立,目视雷神庙,大概有三分钟,谁也没说话。孙乃强担任过二十几年村党支部书记,对抗战时期发生在牟平一带的战事非常了解,更知道我们村有位革命前辈,在这里为了民族解放事业英勇殉国。
那一刻,我不知道孙乃强想了些什么,反正我是感慨良多,思绪万千……敌我双方交战的呐喊声、撕裂空气的尖锐枪弹声、敌人燃起柴草企图烧毁大门的毕剥声混杂在一起,仿佛骤然在我耳边响起。日寇蹿上院墙墙头和房顶的鬼魅身影以及庙内英勇抵抗的勇士们的英姿,一下子全都浮现在我的眼前。那些抗敌的勇士们当中,就有来自我村的张德惠烈士。
张德惠原籍解甲庄街道(现高新区马山街道)新天堡村,祖父那辈上,迁徙至大山后村。
他家境贫苦,长到十八岁那年,听说日本鬼子快打到烟台了,义愤填膺,要去参加八路军,杀敌保国。他的父亲张树公,为人开朗豁达,深明大义,尽管只有张德惠这么一个儿子,但他格外支持孩子的选择。他对妻子和大女儿说,没有国,哪有家?小日本都打到咱家门口了,孩子不去当兵抗日,国家没了,咱也得遭殃!在取得全家人一致支持后,张德惠毅然离开家乡和亲人,跋山涉水,前往昆嵛山,投奔了抗日的革命队伍。
在部队的教育和培养下,他很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侦察员。1938年2月11日,也就是在八路军夺回被日寇占据的牟平的前两天,他奉命秘密潜回老家大山后村,搜集到驻扎在烟台的日军有向牟平增兵的动向等情报,火速返回部队。那时,天色将晚,他行至牟平城东南,听见雷神庙方向枪声大作,经久不息。他判定是八路军跟日本鬼子干上了,顿时血脉偾张,想赶快向首长汇报情报,也马上投入战斗。
张德惠对雷神庙一带非常熟悉,很快便顺着枪声,到了雷神庙不远处,看清的确是一帮鬼子,足有上百人,在进攻庙宇。于是,他瞅准了枪声相对稀少的东面,借着小土包作掩护,拔出驳壳枪,连开数枪,几个日本鬼子应声倒地。小鬼子背后受击,一时被打蒙了,慌乱地向两侧撤退。张德惠趁机奔向雷神庙东厢房跟正房之间的墙头,双脚连续交替登墙,大声喊着:“别开枪,俺是张德惠!”左手把住墙头,拐肘一点,狸猫一般灵巧地翻进墙去。等鬼子反应过来,早已看不见他的踪影了。
他立即向首长作了汇报,在得知理琪同志与多位战友不幸中弹后,他悲恸不已,端着驳壳枪,一会儿钻进厢房,一会儿跳进正厅,连连击毙日寇。复仇的怒火在胸中熊熊燃烧,他舍生忘死,却不幸被爬上厢房屋顶的敌人击中,壮烈牺牲……
这些战斗情景,都是那场战斗中幸存下来的张德惠的战友口述的。
“四哥,咱们该回家去了!”孙乃强的话,把我拉回了现实世界。
车上,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久远的年代——
雷神庙战斗翌日,张树公老人闻听噩耗,犹如五雷轰顶,这个铁骨铮铮的大汉噙着眼泪说了句:俺儿郎为国捐躯,好样的!然后,满怀悲怆地与族人前去雷神庙,为儿子收敛了尸体,葬进了新天堡族茔。
此后,每逢张德惠忌日,老人就要先到祖坟看望先人和儿子,再徒步前往雷神庙,在野外空旷处点上一炷香,烧上一刀纸。
新中国成立后,牟平端午山建起烈士陵园,树起了高大的烈士纪念碑,张德惠烈士与全县为革命捐躯的英烈一道,碑上有名!我早年在牟平师范进修时,去过端午山烈士陵园,亲眼见过包括张德惠在内的我村四位烈士的英名。
自从有了烈士纪念碑,张树公老人便把祭奠英灵的路程,延展到了端午山。年年岁岁,皆是如此,直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
回到村里,送走了孙乃强,我把目光投向小河西边。距离小河百八十步之外,就是张德惠烈士的老宅,我伫立许久,面向这栋老屋,行注目礼……(孙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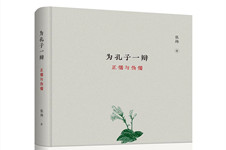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