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这个季节,烟台有一种美食叫海蜇汤。
记得年景好的时候,近海周边到处都是漂游的大海蜇,烟台人喜欢用这刚捞上来的海蜇,做成各自喜欢口味的海蜇汤。赶着海蜇大量上市的季节,喜欢这种美食的人们隔三岔五就“撮一顿”,能从炎热的盛夏一直喝到秋汛开海。有的人家海蜇捞多了,就用土法进行最简单的腌制,等到没有鲜海蜇的日子,今天炒个海蜇头,明天拌个海蜇皮,也能解解馋……
长岛全民参与捞海蜇
1991年的那个秋天,满海满洋漂浮的海蜇来到长岛凑起了热闹,航道上、养殖区、港湾里、礁石边……凡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海蜇的身影。开始人们还都觉得稀奇,看见了就赶紧捞上来,回家菜刀一剁,凉水一拔(方言,冰镇的意思),辣椒、蒜末一拌,再加点醋,纯正的海蜇汤就喝起来。后来海蜇越来越多,再美味的东西也架不住天天喝,三顿五顿之后,哪怕看见再多再好的海蜇也当没看见。
商机往往都是留给那些有头脑的人们的。打一开始,很多的养殖队、个体户都“搂草打兔子当捎带”捞了不少海蜇,回到岸边,左手一把盐,右手一把矾,一层海蜇一层盐或矾,就这么开始了海蜇加工。等到第一批加工的海蜇皮一出手,那些勤快的人家见了回头钱,捞海蜇的劲头更足了。
在渤海湾捞海蜇,是北方捕捞生产当中最简单的行当,既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也不需要什么高精尖设备,只要肯出力,或多或少都能发个财。
那两三个月,我们长岛县从南到北,从渔村到企业,全民参与齐动手,海滩上、码头旁、港湾里,到处是堆积如山的鲜海蜇,到处是加工海蜇的土作坊。生产第一线的渔村和加工企业干不完,就动员后方工副业人员和老百姓加工海蜇。到最后,随着海蜇的捕获量越来越高,几乎所有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都投身到海蜇加工的大军。
我们县委办公室系统有一条40马力的机帆船,加上两位专业养殖人员,就成了捞海蜇的主要力量。人手短缺,时任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孙长文就让有出海经验的人报名上船。
报名的有李希林、方忠鹏、孙明新和我。孙明新高中毕业出海好几年,是我们中间最有闯海经验的好把式。我那个时候已经在南海远洋船上锻炼过了,一般的海况也能应付得了。李希林和方忠鹏虽然没有正儿八经地出过海,但这两个哥们儿长得精干,身手麻利,很有当渔民的潜质。
那天早晨天不亮,我们就从县委大院出发,行政科的刘本平把我们几个送到北长山岛的北城村前海沿。那个时间,东方刚刚鱼肚白,海沿上偶尔有几个出早潮的新式挂机,我们算是起五更爬半夜最早一批出海的人。当年曾经干过“大六百”的船长范国乾,“突突”地开着40马力的机帆船,在彩霞满天的黎明时分穿过庙岛塘,绕过宝塔礁,越过龙爪山,带着我们直插黑山西那边广阔的蓝色海域。

捞海蜇留影,自左至右为船长范国乾、作者、李希林、方忠鹏和一位船员兄弟。孙明新 摄
第一天出海,我们的运气相当不错,碰到了较大的海蜇群,多得一眼望不到边,满海都是懒懒漂荡的海蜇,一个个优哉游哉的,好像是在分享黑山西这一带丰富的“海上大餐”。
对我们来说,这么多海蜇就像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除非懒汉,没有理由不把这些海蜇捞上来呀!
我们这些机关的小青年,干这海上的活没有技巧、光有冲劲,一看见海蜇,两眼放光,擎着捞兜顺着船帮往后撵,瞅准时机,往海里就狠命“吭哧”一下,脚底没根站不稳,整个身子就撞到船帮上。三两个回合下来,膝盖、胯骨、手脖子、胳膊肘……这些地方磕碰得青一块紫一块。开始那几天,今天碰的伤没消肿,第二天接着又摞了上去。返航的时候,大家伙撸胳膊挽袖子比量谁受的伤多,就好像展示“军功章”一样自豪。
熟能生巧这话说得一点也不假,几十个回合以后,各个“工位”上的伙计慢慢找到了窍门。船长范老大专找海蜇密度大的地方开,低速、滑行、漂移,使出一个又一个绝招。我们这几个伙计手里紧紧握着捞兜,好像穿越到古代战场上横刀立马的大将军,在海蜇群里如入无人之境。捞兜贴着船帮,碰见一个海蜇撂倒一个,碰到一个俘虏一个,只要水层掌握合适,捞兜往海里一放,就是一个大海蜇。大个头的海蜇本来就很沉,再加上机帆船前行的惯性,一个人是拿不上来的,都是两个人紧握捞兜的木杆子,一把一把地往上拔。
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们,干这海上的活计还是很欠火候,稍微不注意,就被海蜇蜇了胳膊、扫了脚踝,轻来轻去的,咬咬牙抗两天就过去了,体格差点的,又是过敏,又是抓挠,破了皮就容易感染。吃一堑,长一智,第二天,大家一个个都老老实实换上了长袖衣服,唯恐连续受伤被领导换下。这好不容易争取来的“重要岗位”,屁股还没有坐热乎,怎么能轻易让位呢?
对我们来说,这点苦,这点累,相比捞到满船海蜇的快乐,根本不在话下。那个时间,我们都是二十出头、三十不到的小伙子,从封闭的办公室到坐上机帆船,那种风驰电掣的感觉、那种临海凭风的心境、那种放飞自我的体验、那种丰收的喜悦,怎一个爽字了得!那些苦那些累那些伤,一切的一切都随那渤海海峡的海风飞到太平洋里去了。
“再捞下去,船都要压沉了”
那一天,海蜇多到捞不完,我们一个个也都红了眼,什么口干舌燥肚子饿,早都忘到二门后(方言,忘光了)。多捞一个一块钱,加工出来多挣三块钱,这个不用成本不担风险,就像大海捞钞票一样过瘾。遇见这样罕见的大场面,虽然忙得我们手脚不得闲,但是一个个干得溜欢,不知不觉到了晌午也不歇气,咬咬牙接着干到日头偏西,到最后一直把赶樘里装得满满当当,没法再干下去了,范老大只得说了一声:“还干呢?再捞下去,船都要压沉了……”
于是范老大掌舵返航,我们靠在机舱顶盖上,喘口气,歇一歇。眼瞅着满满一船海蜇,估摸着今天收获的斤数,盘算着卖出去的价格,乐在脸上,美在心里。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满身满脸的污垢和盐碱,一个个“地瓜干子”的模样。最受伤的不是碰伤的膝盖,而是从手腕到整条胳膊的密密麻麻红点子,大家都被海蜇蜇得不轻。有的人皮肤比较娇嫩,十天半个月都恢复不了。
下午三点半,我们开着机帆船满载而归,返回北城前海沿。这个时候的海边,可比早晨热闹百倍。只见浅海水域密密麻麻停满大大小小的机帆船和小舢板,海滩上人山人海,除了干活的人,就是一堆又一堆的海蜇。范老大掌着舵,从一条船又一条船的缝隙中穿插到海滩上,我们从船头直接把海蜇卸到海滩上。
海滩上,简易的海蜇池子一个挨一个,三间房子大小面积的算是小的,稍微大一点的,都是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蛇皮袋子装满球石,垒成齐腰高的“口”字型,大宽幅的塑料布往里面一铺,不漏水,不洒汤,跟正儿八经的水泥池子的效果一样好,省钱省事省时间。
我们几个把机帆船带好缆绳,一个个饿得饥肠辘辘,去找点吃的垫一垫,可是,掀开我们办公室盛放包子的大铁盆,只剩下两三个没有馅、碎成好几块的包子皮。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第一天出海,我们几个没有吃饭的晚上回家一顿吃了两顿的量,有的同志先饿后撑伤了胃,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就犯病,后来就落下个病根,一饿胃就疼,成了名副其实的老病号。第二天,我们几个都长了不少心眼,各自带了凉开水和咸菜、咸鱼、蛋糕、面包、桃酥和馒头什么的,等到傍晌午,大家停了机器吃东西的时候,才发现我们都是“小儿科”。姜还是老的辣,范老大除了带了吃的,还从书包里抠出辣椒、大葱和醋,在那个没有辣根的年代,这都是生吃海鲜最好的配料。你看他就地取材,三捯饬两摆弄,三下五除二就弄了一小盆“长岛好味道”。我们就着馒头点心,不停口地给吃了个“地了场光”。
正晌午“打过尖”后,大伙就像加满油的“195柴油机”,一个个干劲十足,半下午就满载而归,唱着歌儿欢天喜地返航回家。在半道上,我还从摄影包里拿出照相机,和几个同舟共济弟兄们一起拍了几张合影。
1991年的这个秋汛,简直就是送上家门口的“超级好菜”,长岛县从渔村到机关齐上阵,海边捞、海里捞、海底捞。捞一个,回家做个海蜇汤解解馋,捞两个,压个海蜇皮留过年,捞十个,就能卖上不少钱。到了冬天清空了仓库,家家户户“多收了三五斗”,讲实惠的单位,接二连三发了好几天福利,图省事的领导,直接发三百五百花花绿绿的钞票,真真正正过了一个幸福快乐的富足年。(徐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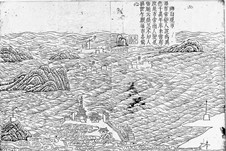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