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一个冬日,天津的同学来烟出差,打电话给我,想见个面叙叙旧。自大学毕业后,我们已阔别一年半之久,彼此间甚是想念。我问他:“你住在哪家宾馆?我今晚就去找你。”他回答:“我住在劳动大厦,就是你们烟台最高的那座楼,南面大坡上有个‘硫’磺顶公园。”
我大笑,纠正他的严重错误:“不是‘硫’磺顶,是毓璜顶,钟灵毓秀的毓。天哪,你一个堂堂的名牌大学中文系的,竟然不认识毓字,太惊悚了吧?”他也跟着哈哈大笑。
那时候,我们的心灵都是透明的。他知道我是在开玩笑,不是真的瞧不起他。
第二天,同学问我:“你们烟台哪儿最好玩?”我说是芝罘岛。于是,我就用刚买的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带着他去芝罘岛。

那时的芝罘岛属于偏僻之地,还没有通公交车。出了城区,跨过铁路,沿着弧形的环海路一路颠簸,自行车哗啦啦响,沿途经过的知名单位有烟台制碘厂、烟渔电子仪器厂、天津航道局等。下午两点多,我们终于进了岛,走进一个黑不溜秋的名叫大疃的小渔村,把自行车寄放到村东头一户渔民家。
渔民是一位中年汉子,一张宽大的脸盘黑得就像他的村子,胡子拉碴的。他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从渔民家出来,我俩往山上爬。芝罘岛的最高峰是老爷峰,我俩就直奔老爷峰。
山越爬越陡,路是没有的,除了大大小小的石硼,便是高高矮矮的松树、柏树,只能拐弯抹角地寻找树木、石硼稀少的地方往上爬。爬得很艰难,浑身冒汗,呼呼大喘,但并不觉得难受,只感到全身热乎乎的,爽极了。那时我们多年轻啊!浑身是劲,能吃苦,藐视一切困难。
爬到半山腰,我们突然看见海了,是芝罘岛的后海。好大啊,海面平平的、蓝蓝的,平得如同虚无、蓝得发青,还有几分神秘的幽深。同学惊呆了,喊着:“吓了我一跳!好美啊!”我跟着说:“美得就像狐狸精,吓了我两跳呢!”浩渺的海面,只能看见一座礁石般的小荒岛和荒岛上一棵孤独的瘦树,不见一艘船,不见飞翔的鸟儿和激荡的浪花,除了海水还是海水,除了沉寂还是沉寂,好像满世界都跟着我俩对大海叹为观止了。
快到峰顶时,我们走进松林中,山风浩荡,疾风入松,飒飒轰响。同学说:“这片野猪林不会无边无际、直通虎狼出没的大兴安岭吧?”我大笑,知道他这个人,只有在极其兴奋时,才会如此幽默风趣。我喊道:“没事!有我这个精瘦的鲁智深给你护驾呢!”他也大笑。
待到登上峰顶,已是黄昏时分,眼看四面都是海。北面的海铺展得最远,极目远眺,视野了无阻挡,似乎能一口气将遥远的大连乃至整个辽东纳入眼中。受到晚霞的涂染,此时的北海,也就是整个烟大黄金水道,不再蓝得发青,不再显得神秘,而是呈现出珊瑚色、橘黄色,温柔可亲,叫人馋溜溜地想起汽水和香槟,想起熟透的香甜的食物或果实。
最令人叫绝的是山下大疃村的西海滩,夕阳下,湿漉漉刚刚退潮的沙滩上,有很多赶海人,远看每个人都很小很小,但生动极了,因为他们都在匆匆忙忙地行走、寻觅。在浅水里,他们留下自己的倒影,又在身后拖着夕阳勾勒的背影。大人们是两条长影子,孩子们是两条短影子,还有时刻不离人的大狗、小狗,它们也都拖着尾巴似的影子。那么多的线条、那么密集的轮廓、那么强烈的动感,既杂乱又和谐,既纯净又斑斓,是我生平从来没有见过的。同学也惊呆了,大声喊着:“这是活了的吴冠中《水乡》图啊,这幅画的名字叫《渔乡赶海》!”
我们大唱大笑,百无禁忌,像两个道童,沿着陡崖下的路,飘飘欲仙地走下山来。同学即兴口占“楚辞”后,兴奋地说:“明年这时候啊,我还来烟台,还来爬这人间仙境的芝罘岛!”我回答说:“来吧来吧,伙计,我还骑着车子带你来。”同学的“楚辞”,我至今还记得:路修远兮到山巅,倚青天兮望大千。海浩瀚兮生豪气,心澄清兮阔无边。
第二天送同学到火车站时,我们都依依不舍,我口占几句打油诗相赠:津门一挥别,海峰尖头立。回望四年事,历历千秋忆。
可是,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我在电脑的“校友录”里翻找到他的照片,发现他头发少了,脸走形了,明显老了。自从那次我们分手后,新年元旦还互寄贺卡,后来就不寄了,不知不觉就断了消息,各自沉入茫茫的人海中。因为工作、晋升、结婚、带孩子、孝顺老人……需要我们操心的地方太多了,其他的都疏忽了、淡漠了、遗弃了。如今在乍然相逢的陌路上,我们可能也互不认识了。如果说起当年的登岛观海,会觉得那是一个梦。
三十八年来,似乎什么都变了。大疃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满村的海草房早已消失了,如今是一幢幢楼房。当年存放自行车的渔家小院早就没有了,满脸胡茬的中年渔民肯定也垂垂老矣。他真是一个好人啊,当我们身披夜色去他家取车时,他邀请我们进屋喝茶,歇歇脚,解解乏。最令人惋惜的当属大疃村西那个水墨画似的大海滩,起先是挖了海滩建虾池,后来又填了虾池盖高楼,再后来变成一个秀丽的居民小区,名叫“西海岸”。一切还会继续变下去吗?我想会的,这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当然,没变的东西也一定有。比如,也许千万年后芝罘岛老爷峰不再险峻、后海不再辽阔,但是它当年的大美,在我心中是永远不会变的。再比如,我对青春时光的眷恋、对同学友情的追念,也一定不会变的,而且是终生不变。(刘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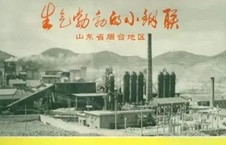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