璜山书院民艺博物馆里有众多的老物件,当看到那台台面斑驳的、色泽深浅不一的老式缝纫机时,我感慨万千,不禁想起妈妈那台缝纫机和她年轻时坐在缝纫机前专注缝纫的样子。睹物思人,妈妈的缝纫机铭刻着时代的痕迹,承载着我们美好的记忆,亲情满满,让我倍感亲切温馨。

一
妈妈的缝纫机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国产“十大缝纫机品牌”之一的“飞人”牌,产地上海,据说是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自主创立的品牌。它可是妈妈的“宝贝”,曾经在妈妈的巧手中为我们兄弟姊妹、街坊邻居和海岛老房东们缝缝补补,可谓劳苦功高。
这台缝纫机是上世纪60年代末的一个春天买的。因为家里孩子多,缝缝补补的手工劳作太辛苦,妈妈早就有买台缝纫机的愿望,无奈全家七口人,只有做军人的爸爸一个人有工资,当时每月的津贴80元,还要拿出30元寄给老家的爷爷,余下的50元才是全家的生活费,根本没有余钱帮助妈妈实现这个愿望。直到大姐、二姐相继工作、当兵后,家里的经济条件好转了,她才实现了这个愿望。
以前经常听妈妈说起买缝纫机的故事。当时爸爸外出不在家,妈妈通过在大钦东村供销社工作的大姐预订了缝纫机。到了取货时,瘦小体弱的妈妈招呼了家里唯一的男子汉——年幼的哥哥,借了一辆小推车,爬陡坡、走山路,特别是要走那个伸手不见五指、连接北村和东村的坑道,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缝纫机运回来。妈妈说缝纫机是花140元钱买的,100多元钱在那个年代可是一笔不菲的花销啊。不过,五十多年走过来,当初这笔花销竟成就了妈妈半个世纪的裁缝手艺,真是太值了。
缝纫机到家后,妈妈先是学着给我们兄弟姊妹缝补旧衣服,过年时才给我们做新衣服。慢慢地,妈妈练出了手,邻居家阿姨和孩子们穿的服装都找她做。
二
妈妈这批军嫂们自打1961年秋天进岛后,因为岛上吃商品粮的单位很少,都没有找到工作。无奈,只好在家洗衣做饭,当“全职家属”。有的在房前屋后开点荒地种上菜,并养鸡养鸭;有的为了挣点钱,上山抓蝎子、捉土鳖、掐黄花菜,或是扒虾、剥鱼子、捡石子、抬沙子,参加公社或驻地村里的集体劳动。后来随军家属越来越多,部队就想办法办家属工厂,起名叫“家属红校”。
“家属红校”成立伊始,妈妈因为有缝纫特长,被安排到缝纫组,每天给部队缝衣服、被褥,非常辛苦。虽然一个月只挣30元工资,但妈妈非常欣慰,毕竟能挣工资补贴家用、孝敬老人了。业余时间妈妈也有不少服装加工的活儿要干,因为周围邻居都慕名前来。妈妈虽然会做衣服,但她大字不识几个。给人裁剪衣服时,量过的那些尺寸,她都是靠记忆记在脑子里,然后再裁剪出来,竟然八九不离十,从未失过手。据妈妈说,姥爷的手就巧,做一手漂亮的木工活。妈妈或许遗传了姥爷的巧手基因。她胆大心细,属于无师自通的“土裁缝”。妈妈还经常把找她做衣服的人的服装尺寸,用整张牛皮纸当布料,提前裁剪下来,再次帮这个人做衣服时,就不用量尺寸了,找出“纸样”比量着裁剪即可。她把这些牛皮纸叫“衣服样子”,一卷一卷放到柜子里,随用随拿。
对这台缝纫机妈妈可“高贵”了,无论每天忙到多晚都要认真清理台面,还经常用机油保养。缝纫机总是放在窗户下阳光明亮的地方,她还用裁剪衣服剩余的旧布头,拼制了一个罩子,每天用完缝纫机后,就打开机器下方两侧的木板,把机头放进木头盒子里,盖上罩子。她决不允许任何人将东西放在缝纫机上面,怕压坏了她的“宝贝”。现在想想,那时缝纫机是家中唯一的大件,是养家糊口的重要工具,的确“金贵”。
海岛的夜晚没有长夜灯,每到固定的时间,部队的熄灯号一响,我们就立马进入睡觉状态,妈妈却急着把煤油灯或蜡烛点燃,她要把剩余的一点活干完,要强的她决不会把当天的活拖到次日。日久天长,我经常发现她的眼睛带着红血丝。
妈妈可会整新词了,她总把做衣服说成“跑机器”或“跑缝纫机”,形象地把机针干活时的状态,用“跑”字形容出来。我小时候过年的衣服,都是妈妈在大年三十下午忙完别人的衣服后,再急忙给我做的。妈妈还挺新潮,我邻居家一个上初中的孩子对穿衣戴帽挺“要好”的,社会上刚时兴穿“紧腿裤”(又称鸡腿裤)时,他就把肥大宽松的裤子,用针线在内侧缝一下,这样穿上后就显得腿很修长了。他妈妈每次给他洗衣服,发现这个手工缝制的线段,就会生气地一把拽下,不让孩子“赶时髦”。孩子再穿时又缝上,妈妈洗时又拽掉,一对倔强的母子谁也说服不了谁,几个回合后,这位阿姨气得跑到我家跟我妈唠叨。我妈一听,不仅没同情这位阿姨,还劝这位阿姨回家把孩子的裤子拿来“跑一下”,别再让孩子费事了。不过,我妈并没有完全按照那个孩子手工缝制的那条线“跑下来”,她折中了一下,让裤子既不像原来那么肥大,又不“紧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基层营业所调回县农行,看见小伙伴们穿衣戴帽都“洋气”了许多,偷偷和小伙伴逛百货大楼买回布料,到当时县城驻地乐园大队一名叫张克仁大叔的裁缝店里做衣服。大叔的女儿亚楠经常在店里,她跟我们很聊得来。她漂亮、高挑的个头,再穿上大名鼎鼎的裁缝老爸做的衣服,让我们羡慕不已。当我取回做好的衣服,偷偷穿上回家后,也不敢在妈妈面前“显摆”,怕挨妈妈骂。因为妈妈会做衣服,还去外面花钱做,我也有深深的内疚感。那天晚上我脱下外套去卫生间洗漱后,看到妈妈在我的房间里扒拉那件新衣服看,我的心立马提了起来。等着她的骂声时,她却指着衣服轻声对我说:“张克仁如果把这个地方再凹进去一寸就更好了。”原来她在研究同行最新的裁衣技术,真是“内行看门道”啊。
三
妈妈带着她的“宝贝”,跟随爸爸在长岛的多个岛屿上安过家。每到一处,时间不长就会有人慕名上门找妈妈做衣服。我发现妈妈最擅长做女装,因为在部队时爸爸他们都有军装穿,用不着做衣服,都是部队家属带孩子们来找她做衣服,做的女装、童装多,久而久之她就熟习了这两款服装裁剪的套路,越来越得心应手了。好像听她念叨过:“男装不好做,特别是凹那四个兜,做起来费劲。”
妈妈会做女装和童装,也让我们姊妹得了大便宜,因为我们家女人、女孩多。后来,我结婚怀孕时,那时没有孕妇装可买,好多孕妇都是穿旧军装,有的孕妇即便不穿军上衣,也会弄条肥大的军裤穿上。我家当兵的人多,新旧军装都有,但我妈妈却买来布料,亲手给我缝制孕妇装,不想让我“优美”的身段淹没在肥大的军装里。我的这套孕妇装闲置时又借给邻居,邻居后来又借给同事,在外面转了好几年,成为好几个宝妈的罩衣。结婚后,我婆婆的衣服基本都是我妈给做的,她俩相差一岁,妈妈一直引导着在农村生活的婆婆穿衣戴帽的喜好,只要妈妈想穿一件什么衣服,买布料时都是买双份,裁衣服时给我婆婆的比她大一码就行。每每我婆婆在老家穿上新衣,都会得到左邻右舍大妈、大婶们的羡慕,说我婆婆找个好亲家,夸我妈妈心灵手巧。尤其佩服我妈妈不用现量尺寸就能给做出合体的衣服。四年前,我92岁的婆婆来看望我父母时,拉着我妈妈的手说:“二十多年都穿你做的衣服啊,感谢你啊!”
我知道妈妈给人家做了那么多年的衣服都是义务的,有时还要搭上缝纫线、纽扣或拉链、挂钩之类的小物件。老妈用过的装针头线脑的铁盒子,现在也被我收藏着,里面做服装的配饰一应俱全。为了让做出来的衣服平整、熨帖,她用过的熨斗就有好几款,有最初那种先用炉火把铁块烧红,再把铁块放进铁槽里的原始熨斗,还有老款不带温度调剂的电熨斗。尽管她做衣服不收费用,但热情、豪爽的海岛人民,也没让她白忙活。每每家里有了鱼啊虾啊或是其他土特产,他们都会想着我妈,我们也跟着沾光,大饱口福。俗话说得好:“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老妈妈活到了94岁,就是性格好,心宽,用海岛话说:“会轧伙人。”她助人为乐的品质感染了周边许多人,当人们称赞“老马大嫂或老王大姐是个好人、是个热心肠的人”时,作为她的“小棉袄”我也会感动。
这台“飞人”牌缝纫机见证了那段旧时光,见证了把青春献给子孙、献给海岛的一名随军家属(老妈)纯朴、勤劳的一生。如今在没有了妈妈的岁月里,妈妈曾经的“宝贝”,以及亲情和思念,我都收藏了下来。(马素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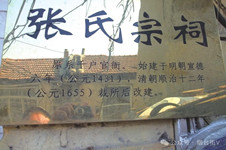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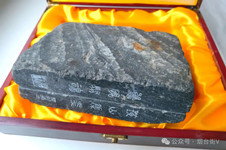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