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望族蓬莱西街孙家的祖上孙应科,在清道光年间入翰林,与樊延枚和王鎏等共同主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嫡孙孙星煜,清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进士。吾族近代与孙家联姻,对其家世略知片鳞半爪。
近日,芝罘历史文化研究会的黄爱杰先生告知,蓬莱第一位公派留学生叫孙继丁,也是蓬莱西街孙家子嗣,并随后发来孙继丁于1976年(时年90岁)撰写的《九十回忆》自传影印版。阅览之余,心潮难已,特别看到孙继丁童年亲历光绪甲午“吉野”号等3艘日舰炮轰蓬莱城的记述,更感觉是弥足珍贵的史料。

甲午战争中的日本军舰 资料图
孙继丁传略
孙继丁,字炳炎。其父孙丽天因家道中落,弃儒从商,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初举家赴朝鲜汉城、釜山谋生,同年9月23日孙继丁在汉城(今首尔)诞生。
六年后,孙家因避朝鲜内乱回国,在蓬莱西街(今钟楼西路)道南行医并经营药铺。孙继丁自幼入私塾,读四书五经,后入登州中学堂,因学业优异被保送入山东高等学堂正科,专修英语,毕业时奖给中书科中书,参加清华学堂留学甄试获备取资格。宣统三年(1911年)入清华学堂,获第三批庚子赔款赴美留学,入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机械系攻读电气工程。学成回国先后任私立南开中学物理及数学教员、南开大学教授;应邀任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受清华大学聘任为物理学教授;被北洋政府交通部派任为津浦铁路济南机械厂工程师兼厂务视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孙继丁超前运作,派员到铁路沿线和煤矿搬运物资和设备,几经辗转至四川广元设立机器厂,同时与陕西省政府合营同官煤矿,使其成为抗战大后方军民的主要能源来源。其后调任国民政府铁路局专门委员、兰州西北公路局副局长,负责将河南省逾2000名灾民从西安运至新疆奇台县安置。
炮火坠年关
据有关甲午海战的史料记载,日军为了攻打威海卫而在山东半岛登陆作战,连续两天由海上发炮轰击蓬莱地区,佯攻作战之后,实则以三万之众在荣成附近登陆,主攻威海卫。日军第一次炮击蓬莱那天,是光绪二十年甲午的腊月二十三(1895年1月18日)下午,当时孙继丁七岁。他记述道:“曾听到震心的炮声、刺耳的弹声从头上飞过,而今回想,我是险遭不测的一人,也可说是大难不死的一个。”
他对这一天的回忆,是冰火两重天的感受——落难的惊恐取代了迎年的喜悦。这天是农历小年,蓬莱的习俗是祭灶,供奉祭品之外还要烧香、点蜡烛。蜡烛是极细小的那种,蓬莱人叫磕头烛。下午母亲让他去买磕头烛,他还没走出家门,惊天的一幕就发生了。他不及门上的倒闩高,正在往门上爬着开门时,忽然听到似乎不远处有轰隆隆的声音,头顶上也有尖锐而巨大的唿哨声,吓得他返身跑进屋里。生病躺在炕上的大哥告诉惊魂未定的他,“轰隆声是日本鬼子发炮打我们,尖叫声是炮弹掠过你脑袋上的声音”。说话间,父亲从北城墙上跑回家,喘着粗气对母亲说:“我看见至少两艘日本鬼子的炮船向城里开炮,快把我给两个小孩子预备的衣服让他们穿上,准备上供的馒头每人给他们背上几个。”他看见母亲给他穿衣服的双手在颤抖,接着父亲嘱咐母亲,自己先带两个小的去逃命,“你在家照顾好下不了炕的老大,你怨不得我们,能不能再见就听天由命吧”。在母亲“不要被逃难的人群冲散”的呼喊声中,父子三人逃出家门。
日落之前,来到南城门口,父亲紧搂着他和二哥挤进水泄不通的人群,侥幸地走出城门,向南奔去。踏着积雪未消的山路,夜行七八公里抵达(南王街道)范家店村,落脚在村西头的关公庙里。他们挤在一铺炕上,父亲心里挂念着城里的妻儿难以入睡,二哥不久就酣睡,而他心中却惦记着祭灶之后好吃的祭品,于是对父亲说:“这时候妈妈和大哥在家吃糖瓜和糕饼了吧?”父亲打了他一耳掴子嗔怒道:“他们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你还在想吃的呢!”他接着写道:“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挨父亲的打。后来自己想想,也真是该打。”
至于前面提及的父亲为他和二哥预备的衣服,那是长辈们在乱世的护幼周全之举。逃难之际,最怕孩子被乱兵和人群冲散,遂为每个孩子誊抄家谱和三代人名称一份,备些许贵重物品,一并缝在各个孩子的冬衣内,以便走散后有人收留和联络。
逃难遇真情
人在境遇触底时,最能感受守望相助的温暖。第二天一早,他们就赶往距城南17公里的(小门家镇)宋家村,离开范家店村头不远处,遇到宋家村李姓忙子哥。原来忙子哥已知晓鬼子炮轰蓬莱城的消息,便牵着牲口往城里赶,接应他们去他家避难,恰巧在此相遇。兄弟二人骑在牲口背上,不到晌午就到了宋家村。第三天,忙子哥又赶着牲口进城,将母亲和大哥也接到他家,一家人团聚无恙,相拥而泣。忙子哥全家人站在一旁,憨厚地露齿而笑。
忙子哥为西街孙家耕种几亩薄田,在庄稼收成的分成上,双方互敬互谅,从未红过脸,素常彼此以家人相待。李家并不富裕,房屋也没有富余,孩子们都住在存储牧草的厢房屋里,睡在草堆上,觉得又软又暖,颇为惬意。孩子们少不更事,背井离乡却度过了快乐的甲午新年,父母的心情则愁闷无解。过了正月十五以后,全家人迁往距宋家村2.5公里的吕家沟村的亲戚邢家安居。父亲传承祖业,从祖父那里研习中医之术,在逃难乡居时经常为乡民义诊,受惠的乡亲病体康复后都会送来米面、瓜果和肉蔬答谢,很快就和周遭的人混了个脸熟。
乡民们的淳朴善良,民间的互助情谊,是人性的光芒,治愈了战争给他们带来的绝望和恐惧,也找到了好好活下去的信心和希望。
童稚观时艰
苟全性命于乱世,却让孙继丁过早地见识了与城里不同的另一个世界,耳濡目染中感受到生存的不易。这也许就是他后来奋发进取,精于学业的潜在动因吧。他们在乡下避难之际,恰是青黄不接之时,却是拾取烧柴的好时节。父兄们入乡随俗,与乡人上山打柴。他因为人小,干不了什么活计,就跟着去玩。玩耍之间,体悟到乡人艰难度日的生存之道。同行的叔叔哥哥们在田头憩息时教他拔豆根玩。豆根本是不准拔出做柴用的,留在地下自然腐烂,即变成肥料。
冬去春来,农民忙着往田里送粪。肥料盛在柳条筐中,左右两个用麻绳捆绑在鞍架上,放到牲口背上驮运。山路崎岖,驴骡驮行,搬运便利,其间夹杂着上山的人流,形成一条迤逦的长蛇阵环绕山际。这期间,孙继丁度过了乡下生活最快乐的时光,他叙述道:“我则坐在鞍子后面的牲口背上,嗅着野花香,听着鸟鸣,好不自在!”
避难期间,父亲时常带着二哥回城打探消息,回来后谈及大哥已订婚尚未过门的嫂子在鬼子的炮击中遇难,炮弹从嫂子娘家正房穿堂而过。他写道:“嫂嫂死亡,也不知是中弹而亡,还是被炮弹吓死的。”他们全家在吕家沟村住到四月底,于端阳节前回到城里西街老宅定居。
他在台湾省追忆这段尘封往事的末尾写道:“当年日兵在荣成登陆,指向威海卫……如今日在台之荣成、文登二县之乡先生们将身经日军登陆与轰击威海卫之详情见告,即可尽知甲午之战山东沿渤海各地所受的破坏与惨状……”这足见孙先生直到迟暮之年,对海峡对岸的故乡依旧念兹在兹。然而,人生的大限决定了他不可能等到那一天,也没有机会去亲吻暌违太久的故土与亲人。
他逃难时驻留过的村庄,一百多年后,村名未改,模样已换新装。这片土地是多么期冀当年的少年郎能再回来走一趟,哪怕是看一眼炊烟、品一口饭香。(张世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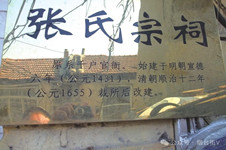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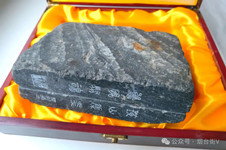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