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开埠后,从烟台山、朝阳街到大马路,是最早形成的繁华地带,遍布中西合璧的建筑。
上世纪80年代以前,张裕公司(也就是现在的张裕博物馆)并不连通北马路,而是紧挨着解放路东的居民区,路西是东陞街和东陞街小学、烟台二院(今烟台山医院);北面是解放路小学(今养正小学);东面是大马路;南面有悦来街、双龙胡同、庆龙胡同和解放路高台阶——高台阶上建有许多高档的民宅,在周边名气很大。
高台阶上几多人家
高台阶坐落在大马路与解放路交会处、张裕公司正对面。从双龙胡同北口以东,一直延伸到市府街东口,由低到高,与富守街直角相连,最高处比解放路路面高出两米多,直上直下,就像一座堤坝,“高台阶”这个绰号就是这么来的。
高台阶上的路面两米多宽,可能是顺地势而建,用石头砌成,铺就水泥路面。在双龙胡同北口向东起步二十米、靠近解放路边,设置了一个不足一米宽的缓坡,方便上下台阶。坡后面一米多宽的高台阶,继续向西延伸到双龙胡同,与后面二层小楼的地基连在一起,就像原来的“堤坝”向后退了一米多。
以后退的高台阶为起点,沿地势自西向东建有二层楼和四合院,与庆龙胡同和富守街的民居连城一片。 高台阶旧貌 解乐达绘图
高台阶旧貌 解乐达绘图
站在张裕公司门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解放路77号院,一栋中西合璧的二层组合建筑,也是高台阶上最漂亮的建筑。小楼地基沿着高台阶用长方形石块砌成,南北对应两座单体二层楼,每个单体一层三个房间,每间一个欧式大窗,西山墙外加一个玻璃窗带木质雨搭子,显得特气派。
南楼六个窗户,开在庆龙胡同内,西山墙两个窗对着双龙胡同转弯处。南北两座楼由西厢的平房连接,房顶铺设专用的木质走廊。在双龙胡同,能看到南楼西山墙和西厢房的窗户,都在约一层楼高的石砌地基墙面上。
转向解放路,地基与斜坡后面坐北朝南的二层楼相连,正对着张裕公司。两层六间屋子带雨搭子的大玻璃窗,在马路上一目了然。院内没有东厢,院墙直接与76号院相连。二层楼的整体地基和靠街外墙均以浅色石条垒成,房间内铺设枣红色木地板,厨房和客厅铺彩色地砖,美观大气。但街门较小,是利用北楼东与76号院的夹道,安装了一扇七十厘米左右宽的街门,有几级小台阶。
北楼一层的大窗户下就是那个向后退的“堤坝”,一个十多平方米的长方形平台,齐腰高,需从77号院的街门边走五级小台阶才能上去,当然,半壮小子一个高儿就跳上去了。春夏秋季的空闲时节,人们在平台上聊天娱乐,男人们下棋打扑克,男孩子们摔元宝弹玻璃球,主妇们则一边聊天一边做针线活儿,因为那里三面都有路灯,比较亮堂。白天,主妇们趁男人们上班、孩子们上学时,插空在平台上晒晒粮食、搓搓高粱米。
那些气派不凡的四合院
解放路76号院是高台阶上最大的院中院。其实,也像一条短街道或死胡同。叫院,是因为高台阶上只有一个石砌的拱形大门框,统一门牌是“解放路76号”。里面三个四合院分别是76号付1-3。
进入拱门,是一条很宽的路,中间铺着宽石条道板,越往里路越宽,到南头看似一堵墙,其实是富守街四合院的北屋,因为对着拱门没开北窗。走进拱门,能看到路西有三个朝东开的油漆大木门,安装的狮子头门环很气派,这是三个四合院。北面第一个院没有厢房,南北屋住了两户人家,与77号院相连。南面两个大门,是标准的大四合院。
虽然是平房,但家家都有天花板,比普通平房空间高,面积大,木框大玻璃窗带雨搭子,地面或抹水泥或铺瓷砖,一个院住三四户人家。
听长辈们讲, 76和77号院都是在大马路一带做生意的富贵人家盖的高级住宅。76号院路东原来是没有门的,是75号院与富守街院的房墙,只能看到厢房的窗户。“文革”期间,75号院一户人家利用西墙头在76号院开了东门,这样他家可以走两个院子。
顺着高台阶往东走,还有三四个普通的四合院,门朝北,有三四级台阶,一个院住三四户人家,西厢与富守街的民居连成一片。高台阶与富守街直角相连,南面有五级台阶上下。台阶下面呈现不规则的十字路,东边是富荣街,通往二马路,西边是市府街,解放路一直向南,在东风电影院南转向东。
危险游戏以及小弟不哭
双龙胡同北口高台阶与解放路路面平行的地方,有一个进入地下涵洞的入口,走下十几级台阶,就进入了从四马路到海边的两个一人多高的大涵洞。除了雨季山洪湍急时没人下去外,春秋冬无水季节,男孩子们经常从那个入口进去,顺着涵洞跑到海边出口。高台阶更是男孩子们的最爱。冬天下雪,他们从坡上往下打“滑溜哧”,几个人摔成一团,“摞儿压摞儿”,笑得前仰后合。
有时,他们还把搬运工人停放在那儿的大板车拉到坡上,一拨儿人坐上车后大撒把,车子凭惯性向坡下滑去,直到触地才停下。然后,合力把车推回上坡,再上车,再撒把——这种游戏,他们会乐此不疲地玩上好多个回合,直到被车主发现叫停,这才罢手。
我小弟长得活泼可爱,半壮小子们喜欢带他玩儿。有一次,正是在玩大板车滑坡时,车把偏了,5岁的小弟从大板车边上甩下来,落到涵洞入口,被边缘磕破了头。
意外发生时,我同学于爱娜正在平台上搓高粱米,见此情景,她来不及多想,擎着被高粱米染得红彤彤的双手一溜小跑到我家报信儿。15岁的我一听,抓起一块纱布就往涵洞口跑。看到小弟时,他竟然没哭,头上的小洞都能看到脑浆了!
我立即用纱布捂住伤口,抱起他就往烟台山医院急诊室跑。大夫一看,直接拿带线的手术针往伤口上穿,我大喊:“怎么不打麻药?”“这样长得好!”大夫话音刚落,伤口就缝合好了,那个麻利劲儿!整个过程,小弟一声未哭,注射了破伤风针就回家了。
正如大夫说的,小弟的伤口长得又快又好,抽线后没有伤疤。没过几天,他又被半壮小子们带到高台阶玩了,还是玩大板车滑坡——不幸的是,这次又出意外了。小弟不小心把脚别到刚停下的车轱辘里了,脚后跟的一块肉被硬生生扯了下来,只有一点皮还连着,鲜血直流。小家伙还是一声没哭。
正坐在平台上织袜子的我听到信儿,撂下手工活儿,抱起小弟就往医院跑。还是急诊室,还是没打麻药,医生抄起剪刀,直接将连着的皮肉一块儿剪掉,用酒精清洗伤口。小弟疼得使劲抓着我的胳膊,也不哭。我问医生:怎么不缝上去?医生说:“缝上去长疤,剪掉了重长新肉,没有疤——小孩儿长得快。”
果真如此,小弟的脚后跟包扎后,只换了几次药就痊愈了。但经过这两回惊吓,大人们再也不让孩子们玩儿大板车滑坡了。
又一起意外之后
同时,涵洞入口的隐患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那是夏天的一次大雨,一个在四马路陡坡边玩水的小男孩儿,被急流带进了涵洞。路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束手无策,有的则拼命往海边跑,守在涵洞出口,期望奇迹发生。
果然,在涵洞出口附近,人们发现了躺在沙滩上的小男孩儿。顾不得他身上沾满了泥沙,人们直接抱起他来就往邻近的二院急诊室跑。经检查,只是皮外伤,可能被水流冲击晕倒在沙滩上,身体无有大碍!奇迹真的发生了。
医院为孩子清洗了身体,进行了包扎治疗。医生分析说,水入涵洞后,因解放路比较平,水流相应减弱放缓,小孩儿便顺着水流,通过又高又宽的涵洞被冲到了沙滩上,没有造成窒息和严重的创伤。
这次大水也涌上了解放路高台阶下的涵洞拾级。或许是因为小弟两次受伤,或许是因为这次大水的警示,有关部门很迅速地用大块预制板盖住了涵洞。
专属游乐场被封印了,男孩们不甘心,几次掀动预制板想“启封”。自然是掀不动的,慢慢地,他们也就不动这个心思了。
上世纪80年代,高台阶消失了。留下的,只有记忆了。曾经家住这一带的人们,关于高台阶,你们还记得些什么呢?(高守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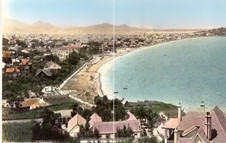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