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曦撩开夜幕的轻纱,天未放亮,我便匆匆起床,带上游泳的家把什,赶最早一班公交车,去第一海水浴场。每每在一中站点上下车,挤在衣袂飘动的中学生堆儿里,总会勾起自己上学的过往。当年烟台一中的文娱团种种,在睡梦中长势蓬勃,长成了坚固的记忆。
花儿与少年
人,永远去不了的地方就是过去。回忆,不是为了抵达,而是为了梳理。现在的学生若回忆学校生活,离不开沉重的书包、烧脑的考试,而我们作为一中文娱团曾经的成员,回忆中更多的是全面发展的丰美枝叶:
每天下午最后两节课,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到操场上打球、跳远、跑圈。文学社团由王焕章、陈兰英老师把关,双周出刊一期四大黑板的《火箭报》,文字插图美得让人心悸;生物组到后山的养殖区,随郭都邦老师汲取成长不可或缺的“叶绿素”;理科组在化学教室随蔡致远老师做蒸馏实验;各个体育专项校队,在孙知非、刘鹏飞老师指导下集训;鹿道澄老师总会在葡萄架下的音乐教室,监督文娱团的排练……
我是1956年上的一中。新学年伊始,高八级的刘百昌和绰号叫“青岛”的学长,到操场上物色文娱团成员。他们看正在打球的我和贺永宜挺精神,便记下名字和班级。考察中,了解我是学习委员,贺永宜是班长,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便吸收进入文娱团。
新团员先放到学校合唱团预热。合唱团由郭祖荣老师牵头,他调福建音乐学院任教后,由孙忠安和谢箴厚老师负责。郭老师作曲、谢老师作词的童声合唱《小松树》,获奖无数。
每逢纪念抗战胜利,孙忠安老师指挥的《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八个乐章,一气呵成。雄迈的鼓点、嘹亮的歌声、豪壮的呐喊:“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音乐史诗,以及潘宝昌、丁岩出演的《放下你的鞭子》街头剧,撼人心魄,荡气回肠。
初入文娱团,我分在舞蹈队。刚开始跳舞,手脚无处安放,举步投足连自己都觉得别扭。特别是集体去26军宣传队学习舞蹈《花儿与少年》,更让我露怯。这个舞蹈融入中国西北民间“花儿”的舞步,基本动作是左手卡腰,右手持扇,起步时双脚脚尖着地,右臂挥扇;收扇时放下脚跟……动作有起有伏,绝对不能舞着扇子一抻一抻地往上“钻够”。
说起来容易,协调好,很难。走队形时,因为我个子高,还和女同学任玉玫一道,被选出来跳“大对”,经常有领舞的段落,这更增添了不小的难度,逼得我经常回家跑到凉台上偷练。
那个年代,烟台尚没有专业歌舞团,有外事接待任务,大多是烟台一中文娱团出演节目。《花儿与少年》排练成功,市里抽调我们到烟台山下的交际处为来宾演出。手持大红折扇,身着民族服装,随着乐队演奏的青海《四季歌》,翩翩起舞。演出谢幕时,得到苏联专家的赞扬:“оченьхорошо(很好)。”我们当时学的就是俄语,异口同声回答:“спасибо(谢谢)。”
《花儿与少年》的高光时刻,出现在几十年后,1991年烟台一中建校60周年校庆晚会上。
准备晚会时,谢新柳老师通知往届文娱团的同学返校,准备校庆演出。各届同学一呼百应。我工作抽不开身,个人又多了些矜持和禁忌,找了许多理由,请假才被批准。
校庆那天,我早早坐到台下为老同学捧场。“下一个节目:舞蹈《花儿与少年》,演出者:文娱团老团员。”报幕员让我们掌声欢迎平均年龄56岁的“花儿”与“少年”倾情登场!
随着乐声响起,6位大腹便便的“少年”和6位腰如水桶的“花儿”,踏着轻快的舞步刚一露头,观众席立即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尖叫和呐喊,激动得我眼窝里溢满泪水:“女儿家的心上呀起呀么起波浪呀,小呀啊哥哥呀……”
全是真功夫
那时,一中文娱团绝对是市里群众文化活动的主力。凡专业剧团来烟演出,艺术馆都会抽调一中同学前往学习。在中央歌舞团来烟时,我们学了《游击队舞》《服务在田间》;我们还向省歌舞团学习了快乐俏皮的《游春》和以鼓子秧歌为基调的《迎春舞》。
学校每年都组织学生助农,文娱团同学单独集结,轮流到各村宣传鼓劲。溪边搭台,星光满天,真有唐诗“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的意境。
舞蹈《服务在田间》实景演出。我们扛着农具登台,社员会心的微笑洒在开满山花的田埂上:“不逢节,不赶集,抗旱前线修机器。老师傅,浑身汗,老支书,满脸喜,眼望着水泵吐金龙,四只大手握一起”……
演《游春》,4名女演员好选,男演员必须能打“小起身”。我们几个男同学拼命练功,都想一试身手。结果孙国光、徐东瑜、杨仍惠、梁圣玺同学抢得先机:载歌载舞中,男生忽然倒地,接着来个鲤鱼打挺,飞身追逐,欢快俏皮……我练成“小起身”晚了一步,与心仪的舞蹈失之交臂。
“七一”晚会,赶上我准备中考,没时间参加排练,可演出时少一个人,让我顶上。演出地点是后操场图书馆楼前的土台,台下全是熟悉的同学。《游击队舞》是我到中央歌舞团学的,轻车熟路,出场前对了一遍音乐,匆匆上场。
10个男同学穿上对襟布褂,头扎白色毛巾,每一次卧倒,每一回刺杀,每扔出一颗手榴弹,动作整齐划一,威武敏捷。可跳着跳着,因为他们擅自改动了队形,却没跟我交待过,显得我跟不上节奏,台下同学笑话我丢人显眼。我不免委屈,却也有意外收获,从此领悟到世事真伪难辨,是非曲直,经常会被篡改,清者自清,辩无可辩。
虽然演出偶有失误,可我也有救场的灵光一现:在门楼水库工地演出《老货郎》,临上台,扮演书记的同学突然嗓子说不出话来。谁来顶替?鹿老师马上找到我:“你来!”
当台上的老货郎挑着担子下场时,我被匆匆推上台,急忙喊道:“厅长!厅长!他走啦?”台上人见我上来了,先是一愣,回过神,继续念台词,齐声问:“谁呀?”
我马上回答:“唉?刚才那个老货郎是咱省商业厅厅长啊!”大家作恍然大悟状,齐唱:“噢,原来是商业厅长下了俺乡啊,原来是商业厅长下了俺乡……”
演出成功,被同学们称赞。之所以临危受命,我猜是因为收工时,我用普通话给一个同学背诗,被鹿老师听到,紧急关头派上用场。
鹿老师管理文娱团像他教数学一样,细心耐心。经常用几何中加辅助线的方法,破解排练中的难题,也会像在课堂上演算数学公式,为学习、活动两不悮,计算着成功指数和时间成本。歌舞排练,他总能说到点子上:“动作的和谐,是身体的和谐,也是几何、数字与音乐的和谐”;“老师的双眼像直尺和量角器,把握着精益求精的关口”。
年近半百的鹿老师率文娱团,利用暑假到福山剧场公演,票价5分钱。文娱团第一次将贺永宜设计的新颖海报,张贴到县城的大街小巷;第一次承担舞美、服装、道具、装台等重任;第一次把闽南歌舞、山东秧歌普及到夹河之滨;第一次食宿在剧场,女同学睡台上,拉上大幕;男同学在台下的排椅上,做着美梦。
公演的舞台大红大绿,却并不庸俗。团长王文苑小提琴独奏《新疆之春》,具有浓郁的维吾尔族音乐风格,跳弓、拨弦,节奏明快地抒发了解放后新疆人民欢欣酣畅的生活情趣。于宝箐的板胡独奏如行云流水,高潮时,转急急风,激起观众共鸣,屡求返场。邢云庆的唢呐独奏《百鸟朝凤》,变化多端的鸟鸣,如花腔的情歌,如山水的咏叹,撩拨着观众的心弦。《十大姐》《春到茶山》,民族风味;本地自创舞蹈《绣花舞》《夸地瓜》特接地气;《荷花舞》则是古典美……
表演唱《娶了媳妇忘了娘》《五个女儿五朵花》《合作社就是好》,特别是于进华、张昭华、张丽华等女声四重唱《红莓花儿开》《深深的海洋》,既有曼妙的抒情,又有声部的爆发。
孙国光等表演的舞蹈《莲花灯》,集体亮相后,拉下电闸,随着音乐上下穿梭的灯海,波涛汹涌,演绎着龙摆尾的惊艳动画;《红绸舞》挥着大车轮,追逐“福”,缠绕山,长虹直甩夹河边;
丁岩和康宝的表演唱《新人新事出在新国家》,一开口就是“老两口同年哪五十八呀哈,越活越觉得劲头越大哈哈”,赢得掌声一片;孙尧德独唱《老司机》、王致仁等主角荟萃的歌剧《花好月圆》,颇受观众爱戴;
压轴大戏是王英珠、丁岩、康宝主演的吕剧《袁樵摆渡》,仙女在梁圣志制作的焰火中亮相,画面充满惊艳之美。
一中文娱团就像闻名全国的“乌兰木骑”,音乐舞蹈、相声小品、戏剧器乐,十八般武艺,全是真功夫。
文艺是精气神

文娱团部分成员参观一中校史馆
(中排左三为本文作者)
有人可能会觉得这帮学生怎么如此不务正业?其实,恰恰相反,尽管丝竹管弦,尽管笙歌曼舞,同学们却都明白“学习是主心骨,文艺是精气神”,都相信“点豆是豆、种瓜得瓜”。
好多文娱团同学考上重点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姜大维、华东纺织工学院的梁圣志、天津大学的贺永宜、上海交通大学的郑道齐、北京邮电学院的杨述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邢建、中国音乐学院的梁秀凤、山东理工大学的孙国光、山东师范大学的刘淑英、山东大学的潘宝昌、孙嘉宾、杨仍惠、王振茹,还有进入国家田径队后在大学任教的曲敬祺……
进入专业剧团的同学更数不胜数:前卫歌舞团的张增爵,长岛吕剧团的王英珠、二炮文工团的林艺、于宝芳,山东歌舞剧院的刘振璞、梁秀凤,山东省话剧院的丁丽华、王有刚,潍坊歌舞剧院的王文苑,烟台歌舞剧院的丁岩、秦培基、王致仁、慕学兰、张昭华、牟英杰。进入群众文化单位的孙忠安、谢箴厚、康恩宝、张最玉、韩笑梅、张广太,还有在美国旧金山业余合唱团领唱的夏安宁……
中学6年的精神哺育,文化学习与文娱活动像牛奶与面包,全面的营养滋养着我们成长。
丁岩是文娱团的资深学姐,我们曾住前后胡同,我和她小妹丁莉同班,经常到丁氏三姐妹家里上晚自习。我为了写作此文,和丁岩通过电话。那天恰巧又在公交车上邂逅,她说刚参加过市里老年模特队排练,并马上拿出一个小本子,接着谈一中的话题。我不知不觉坐过了站,她马上撕下小本子上所有关于文娱团的记录交给我。
我一路沉浸在丁岩的侃侃而谈之中,八旬老妪一点没有“朱颜辞镜花辞树”的感觉,意兴飞逸的劲头,令我羡慕:“一个人有怎样的生活态度,就有怎样的人生风景”,这难道不是她年少时在文娱团活动的精神积淀?
马尔克斯说:“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几十年奄忽而过,中学生活那沁人心脾的华彩乐章,像一幅油画镶嵌在记忆深处。
文娱团每排练一个节目,门前的葡萄藤就长出一段新芽;成功上演一台晚会,总有葡萄满架的喜悦。文娱团门前的葡萄架,缀满我们斑斓的青春:在《袁樵摆渡》的人生海洋中,用《黄河大合唱》的火炬,点亮心中的《莲花灯》……
文娱团同学每逢聚会,告别时,总是恋恋不舍:春风已经吹起,心中满是欢喜,记得来年相约,葡萄架下等你……(尹其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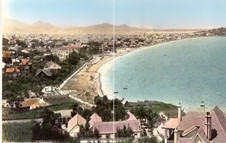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