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入了冬,刮西北风的日子就多起来了,这是由胶东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决定的。打我十几岁开始,天越冷,风越大,刮的时间越长,心里就越高兴。因为我知道,接下来就是“西北风落脚洘大潮”,冬季里赶海的最佳时机就来到了。
不是海边的人,想像不到“风落脚”是啥样,那应该算是大自然的一场魔幻表演:养马岛前海滩的水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连港(方言读音jiang)渠里的水也退下去好多,站在边上往下看,如同站在悬崖边上,让人眩晕。
那时候,海产品特别丰富,每当遇上这样的大潮,我们都要“挽起眼毛”(意同“瞪起眼来”)大干一场。
“西北风随日落”,潮水随着西北风的慢慢消停哗哗地向后退,从滔天巨浪变成了抽底的浪涌子,浅滩的海肠子、沙蛤、花蛤、驴蹄蛤、血蛤(大毛蚶)、海参、“老头蛋”、蚍蛴、蛏子等等,都一股脑随着浑浊的海浪向岸边滚。

我们一个个穿着齐大腿根子的高腰水鞋(半腰水鞋用车内胎一圈一圈绕着粘起来的),拿上捞捞(手操网兜),破棉袄用绳子捆住,棉帽耳朵捂紧了,带着手电或嘎斯灯,随着潮水大步流星地来回跑,每每都是收获颇丰,连养马岛西山头的天然海参也不是什么稀罕物。如果正好在年根儿能赶上这么一潮“风落脚”,过年时招待客人的菜肴就会极其丰盛。
听父辈们讲,当年家乡不少人在高丽(朝鲜)开饭店,每年都趁着冬季的“风落脚”,到海上抬回几筐海肠子,回家晒干了碾成面儿,做菜的时候撒上一点,就和时下用味精一样,做出的菜肴格外鲜美。
有一种蛤蜊叫瓷蛤,因其壳薄薄的易碎而得名。其个头形状酷似鹅蛋,也叫做鹅蛋瓷。它生活在靠近港渠的海滩,一年中难得有几次退出干滩的时候。那里的瓷蛤长得格外肥大,瓦灰色,最大的三个就够一斤。
挖瓷蛤要有一张称手的铁锨,我们那时多用从大连捎回来的钢板锨,每边裁去一小条,再到铁匠炉把刃口擦上生铁,既轻便又锋利。
瓷蛤的洞穴大约有四五十厘米深,顶面留有气孔,间或向上喷出一股海水,通常叫做蛤窝。随着潮水哗哗退去,海滩上立马就结成了铮亮的一层薄冰。由于瓷蛤不断喷水,就在蛤窝周边形成一个圆圆的小水洼,很容易辨认。
动手挖瓷蛤要讲究技巧,如果是个力巴头,一铁锨下去,用力过猛,很容易就把瓷蛤挤碎了。看那些有经验的老手,先在离蛤窝十几厘米的位置垂直把铁锨插下去,手上用力斜着把沙土提上来。紧接着,再沿着这个位置深深的一铁锨下去,用力向前一掘,一个鹅蛋般的大瓷蛤就囫囫囵囵地露出来了。
这个营生既要眼明手快,又要拼体力。那时候,我们习惯把挖瓷蛤调侃为“撂粪”(从猪圈把土粪扔出来),算下来,这小半天的工夫,最多时一个人能挖四五十斤瓷蛤,大约至少也能撂六七圈粪了。
家乡的蛏子也很有名,其形状就好像两片破开的竹片,习惯上叫做竹节蛏。
在庙江西边有一小片沙滩,是有名的蛏子窝,那里的蛏子又多又大,可那片海滩轻易退不出来。只有每年的数九隆冬,连着几天的大西北风落脚后,才会露出滩来。从退潮到上潮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两个多钟头。
蛏子平日里生活在浅海中,它的洞穴大约有四五十厘米深,只要有一丁点动静,它立马就缩进了洞穴的底部,要用蛏子钩才能逮上来。可遇上这罕见的风落脚,在潮水退下去的瞬间它就被冻得麻木了,等听到动静想要缩进洞穴时已经力不从心了。

挖蛏子的时候,铁锨也要垂直下去,向上提的时候手腕一抖,一只只拇指粗细、十多厘米长的蛏子就一排排立着出现在眼前,那简直太过瘾了,用我们的话来形容:那就和拔豆棍儿一样。
每当屋外刮起呼呼的西北风,就想起了这些往事,可也只能当作故事说给孩子们听了。举目望去,我们当年赶风落脚的那些地方,如今都是高楼林立了。
还想起一件事要说清楚,“风落脚”一定是指西北风过后退大潮,千万不可把东北风混为一谈。海边人还有句谚语专门形容东北风———“东北风,十个篓子九个空”,意思就是说只要刮东北风,绝对退不出好潮来,赶海也不会有收获。
本文由孙世林/口述 刘甲凡/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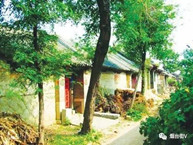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