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挑着担子进养马岛卖菜,牟平人称之为“过岛”。
养马岛可耕地少,岛民不是外出经商,就是下海捕鱼,生活相对好于岛外。有顺口溜:“养马岛,地方好,吃片片,穿棉袄。”但岛上农产品匮乏,加之交通不便,蔬菜价格必然高于岛外。而岛外的农民日子过得苦,种点蔬菜自己舍不得吃,只想去养马岛卖个好价钱。每年三四月份,进岛卖菜的络绎不绝。我叔叔唐续桂(人称唐桂)就是过岛的常客。

我们是东油坊村人。记得1943年,我7岁时的一个早春,叔叔要过岛。头一天,夕阳被几朵乌云遮掩,昏暗中,叔叔撅着筐,里面放一把刀,腋下夹着一条长凳,径直向菜园走去。我拐着篓子跑步跟在叔叔身后。
到了菜园,放下工具,他麻利地从菜窖里搬出十棵大白菜,脚蹬长凳精心修理。拿起一棵菜,首先扒掉第一层帮,再把菜头上的黄叶、烂叶“嗖嗖”地用刀削掉,留住底帮呈梭子型,然后用稻秸一捆就算完成了。
一会儿,十棵菜拾掇得很漂亮:鲜嫩、翠绿、晶莹、真像一棵棵碧玉。叔叔分装到两个筐子里,每筐五棵,四棵立在筐下围一圈,一棵躺在最上面,然后用草绳在菜周围一绑,一担菜就备好了。临回家时,叔叔又从菜窖里拿出一扎香菜放到筐子里。
我把叔叔扔下的菜帮拣起来,去掉枯叶、烂叶,放到篓子里,自家做菜吃。
第二天一早,叔叔把我叫醒,答应带我一起过岛,我高兴得跳起来,急匆匆地吃了几口饭,随叔叔上路了。
春寒料峭,脚下的路冻得硬邦邦的,天虽冷,但叔叔脸上的汗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他不时地用一只手拿块白布擦着汗水,另一只手扭转着扁担,一边走,一边换换肩。扁担“吱呀、吱呀”地响,从敞开的领扣里,能看到叔叔红肿发紫的肩膀。
从东油坊村出发到盐滩村渡海口足有七里多路,他没有喘息,一口气到达目的地——“吕七口渡口”(音),可惜又遇退潮,小船不能停靠,必须经过大片的海滩到海渠子水深的地方上船。于是叔叔又挑起沉重的担子,跋涉在海滩泥泞烂草里,一步深一步浅地行进着。
跟叔叔一起的还有邻村的王伯伯,叔叔称他王哥,他们好不容易奔到小舢板跟前,只见船帮上搭了一条窄窄的长木板,叔叔和王伯伯挑着担子颤悠悠地走上了小船。
一会儿小船启航了,船公一面摇着橹一面唱:“小舢板,摇呀摇,风别狂,浪别跳,大家好好歇歇脚,我送菜友去过岛,卖菜换个肚子饱……”船公弓着腰迎着逆风吃力地摇着橹,终于到达对岸。叔叔和王伯挑着菜担各自向不同的村庄走去。
叔叔进了黄家庄,沿街叫卖:“卖菜啦!卖大白菜——”妇女们听到这熟悉的叫卖声,纷纷走出了家门,你一棵、我一棵,大白菜一会儿就被抢光了,只剩一扎香菜。此菜初春稀缺,价格昂贵,很少有人问津,只有一位胖叔叔蹲在那里一棵一棵地挑选。
这时,坐在石台上的一位老爷爷守着一棵菜对叔叔说:“唐桂,你卖的菜是正宗的胶菜,心儿多,味儿鲜,加上秤儿足,价格合理,大家都愿意买你的菜,别忘了多留点菜种!”
正说着,迎面走来一位黄奶奶,含着眼泪说:“唐桂,我孙子生麻疹了,香菜根烧水喝,疹子会很快出来,病就好了,我跑了很多地方也买不到……”叔叔知道她儿子有病,家里很穷,二话没说,把香菜免费全部送给了黄奶奶。叔叔有感触地说:“我的女儿名叫‘小根记’,五岁时肚子鼓胀,有人说得了‘馋脾’,后来又生疹子,孩子丢了……”说完泪流满面,催黄奶奶快回去给孩子治病,黄奶奶感动地说:“谢谢,你给俺救急,善有善报……”说着一溜小跑回家了。那胖子叔叔瞪了我们一眼,气哼哼地空手而返。
回家的路上,叔叔给我买了一支糖葫芦,又酸又甜,好吃极了,这就是我喜欢跟叔叔过岛的想头。叔叔又从衣兜里摸出几头蒜,在路上换了几盅“雀雀”(一种迷你海螺,也有叫海锥、海瓜子的),回家给姐姐堂妹们解馋。
正准备原路返回,不料远处又跑来一位杨婶,气喘嘘嘘地说:“你明天务必捎点香菜来,我外孙女生疹子,正发烧,你救救她吧!”叔叔答应明天一早亲自把香菜送到她门上。杨婶把我们送到小船上,小船离岸了,她还在远远地张望,不断地挥手。
我们回到家里已是下半晌了,叔叔一进门就把过岛卖菜的钱“哗啦”一声全倒在炕上,爷爷眯缝着眼睛一张一张数着,叔叔又把“雀雀”交给姐姐妹妹们解馋去了。
奶奶知道我们肚子饿了,从锅里端出一大盘地瓜干和半小盆煮大白菜帮。我和叔叔一会儿把饭菜扫个精光。奶奶指着我遗憾地说:“看样子没吃饱吧?我该把你拣的菜帮多煮一些的。”说着转身进了里屋,吩咐爷爷:“首先去买火纸,没有它晚上就不能打火做饭了,剩下的钱全买地瓜干,今年春脖子长,咱不能扎脖梗啊!”
我和叔叔马不停蹄地又去园里做明天过岛的准备,较之昨天,筐里多了两扎香菜。
夜里,不知什么时候,叔叔悄悄地挑着担子出发了。天亮了,小北风嗖嗖地刮着,有时还飘着几朵雪花,奶奶念叨着:“天不好,小船能通吗?”
果然天快晌了,叔叔挑着担子回来了,哭着告诉奶奶:北风越刮越大,小船走不远,突然又来了一阵巨大的旋风,风大浪高,小船被风浪卷到高空,又摔了下来,倒扣了,船上的人全被海水淹没了,“邻村跟我经常一起卖菜的王哥连菜带人全没了踪影!”说着,叔叔跺着脚嚎啕大哭,全家人都跟着抹眼泪,奶奶说:“这该死的海水像个饿鬼,自古以来翻了多少船、吃了多少人啊!它横挡着进岛的路,什么时候能有一座桥啊!”
一连几天,大风连巨浪,小船没法通航。后来听说,黄奶奶的孙子好了,杨婶的外孙女却离开了人世。没能及时过岛送去香菜,叔叔很难过,自责了很久。
叔叔过世已有三十多个春秋了,解放后,他担任过东油坊村的村长兼党支部副书记。可惜他走得早,没有亲眼看见如今“一桥飞架南北”,大海“变通途”的盛景。
虽然“过岛”二字早已消失了,但这段历史不会从记忆中抹掉。叔叔在天有灵,看到养马岛如此巨变,一定会感到欣慰的。(唐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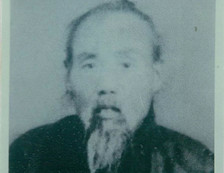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