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缸、纸盆、纸盒,这三种器具,过去是胶东农民家家必备的,都是主妇们亲手制作的。我母亲是制作纸器的高手,她做这些器物时,我替手垫脚地帮过忙,那些场景都还记得。
我们村西的香山沟,有个出黄膏泥的地方,叫黄泥台。村里的人都去那里取黄膏泥制作纸缸。我也挑着担子去取过。把取回来的黄泥块砸碎,和上麻刀(就是把破麻袋用铡刀铡碎,再用木棍敲打蓬松)、碎纸一块浸泡,反复搅拌成粘稠如糕的泥巴。这就是制作纸缸(我们叫打纸缸)的原料。
打一批纸缸,常常是一二十个,甚至是二三十个(有时分送亲戚或邻居)。母亲用选好的大小陶缸做胎模。她把陶缸反扣在平地上,先糊上一层纸,再往上贴泥巴。母亲系着短围裙,一条蓝布巾裹头,挽起袖子,揪一块泥巴,用手掌拍成饼,“啪”地贴到缸模上。接着用手掌拍打,使厚薄均匀。随后还要用戗锅的铲子轻轻拍打,使之表面光平。
这样一饼一饼地贴,一铲一铲地拍,直到把整个缸模贴完,最后将缸模移到日头地里晾晒。晾干了,就可以取模了。母亲小心翼翼地将反扣着的缸模翻过来,遍处轻轻地拍打,使缸模与坯缸分离,再抓着滚圆的缸模边沿慢慢扭动,最后,把缸模慢慢地轻轻地提出,真如金蝉脱壳般,一个崭新的纸缸就脱出来了。
经过大约两三天的工夫,院子里便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纸缸坯。下一步便是整修和装饰。纸缸边沿毕竟是粗糙不齐的,母亲用剪子修整好,就开始糊纸和布。纸缸的内外壁都要糊上布和纸。母亲用地瓜面打浆糊,为防止虫咬,里面还要兑上白矾。厚厚的一叠,洗得干干净净、熨压得板板正正的破布片早已准备好了,母亲先用这些布片在纸缸内外糊上一层,接着再糊上两三层破书纸或“鬼子纸”(当地人把英文报纸称作“鬼子纸”)。如果是准备给女儿做陪嫁用的,还要特地糊上桃红色花笺纸。
纸缸主要是用来盛米面的。那时小麦产量极低,一亩地(老亩,一亩顶现在一亩半)产150斤就认为是大丰收了。因此,纸缸即可满足储装。
纸缸要有个缸盖,以便遮蔽尘灰和防潮。做纸缸盖用的材料不是泥巴,而是席片,是从破席上剪下来的。母亲把破席用水濡湿,拣着可用的地方,剪成作缸盖的条条片片,然后用线缝接起来。缝好的缸盖再以布片和纸糊起来。若是准备给女儿作陪嫁用的,还要再做点装饰,在盖的上下边沿,剪贴上锯齿状“黑牙字”,顶上再贴双喜字。
最大的纸缸盛装分量约有四五十斤,最小的也就四五斤。每个农民家庭都拥有这样大大小小的纸缸一二十个,甚至更多。纸缸形体小,分量轻,又便于移动,很适宜居家使用。质量好的纸缸,用手拍拍,能发出一种韧健而富有弹力的“咚咚”声。若仔细使用,一辈子够用,甚至传辈。
做小纸缸,胎模要选造型优美的花鼓式水坩(农家常用的一种盛汤水的小陶器),取其下半截,仍以黄泥为原料,制作程序与大纸缸相同。小纸缸多用来盛装烙煿好的面食或枣、栗、花生等。

村东干涸的泥湾里人们抛弃的纸缸,这几个品相还挺好呢。
过去闺女出嫁,都由娘家陪送一套由大柜、桌子、箱、几、瓷器等组成的嫁妆。出嫁头一天,婆家的人来抬嫁妆。抬到半路歇息时,便由挑瓷器的人拿出钥匙(钥匙是新嫁娘授给的),打开大柜,掇出一个器物,从里面取出格子馃子(煲煿的面食品)等喜品分给大伙吃———这是一条老规矩,那盛喜品的器物就是那小花纸缸。
抬嫁妆的人也都知道一个“秘密”:箱里还有两个花纸缸,装满了更好的喜品,但那是不能动的———这也是一条老规矩,因为那是新娘准备给新郎、公婆、小姑小叔吃的。
糊纸盆的材料主要是纸壳、破书纸、麻刀,掺上少量黄土,加水一起浸泡,搅拌成稠稠的纸浆。通常以大陶盆(俗称“大锅盆”)为胎模,制作程序与纸缸相当。大纸盆的直径约有六七十厘米,壁厚约半厘米,轻便而有弹性,主要用于覆盖在炕上发酵的饽饽之类,还可用来罗面、临时盛装东西等。
做好的纸盆,里外都要用布片和纸糊起来。讲究而又手巧的人家,盆外糊上花纸,盆底边和盆上沿处,剪贴上索链或黑牙字。我的母亲既讲究又手巧,我们家的大纸盆就是这样的。
纸盒,是用旧席片做的,做法跟做纸缸盖相同。特别要提一句的是,给闺女作陪嫁的那对大纸盒,外面一定要用鲜艳的桃红花纸糊,盒底和盒盖上下边沿要剪贴黑牙字,盒盖上面贴黑色大双喜字,四角还要铰贴上蝙蝠图案,以示吉祥和富贵。
过去在农村,婚姻说定之后,由男方下聘礼,即“定亲礼”,俗称“送笸箩”,那笸箩就是贴着双喜字的大纸盒,里面装着绸缎面料和钱,用大红包袱裹着,由媒人送到女方家,再用这笸箩装着女方的回礼(通常是帽子、腰带和鞋)送到男方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集市上还看见有老太太守着几对精致的花笸箩卖,无人问津。这以后,就连影儿都不见了。(王芝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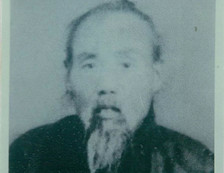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