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花甲,余心未老。近日,聆听年轻歌者河图的《山河永慕》,被其摇滚加古风的韵律所打动,当听到“来也凛冽去也孤绝,动如参商不须别”时,更触动我心弦,一段尘封往事也跨越时空再度浮现脑海。
上世纪60年代后期,始建于明宣德年间(公元1426年前后)的蓬莱大忠祠位于当时尚存的鼓楼东侧、画河桥西南一隅,供奉列祖神位的主体殿堂——祖堂(坊间称“大殿”,清宣统三年原址翻建,宏大于昨)坐北朝南,虽建筑平实,但名声显赫,典藏丰富。在“破四旧”中,大忠祠内置之物和周边陈家人的家藏文物被损毁,弃于画河西岸河套里,垒成丘而焚烧殆尽。
那时,蓬莱百姓的一日三餐全都仰仗柴草烧制,画河边未燃尽的木条和字画、书籍的纸张被周围村民抢拾。为人间烟火提供余热,是从这些有着几百年文化积淀的文物身上所能榨取的最后价值。我父也不例外,也曾拿着麻袋将文物残羹捡拾回家中。其间,他偶然发现一块长56厘米、宽28厘米的红漆描金、镌刻着“鸿禧”两个楷体金字的牌匾。我父带回家并询问祖母,这是否是陈家的手泽。祖母端详良久说:“给我留着,是个念想。”

父亲捡回来的挂匾
祖母陈秀娟的父亲陈命书是大忠祠陈家第十六世孙,育有一子两女,祖母是次女。直至多年之后,祖母才道出真相——这是祖母娘家一支的一块家用挂匾,从挂环的形状上可以辨识出。
这种形制的挂匾在蓬莱的各个祠堂和大户人家都有,但取词各异,规制也不同。陈家的挂匾尺寸不大,秉承陈家一贯低调的祖训(就连大忠祠临街门脸建筑也要比其他民宅往里凹进去3米,避免给人以“出风头”的印象)。在新年伊始、新居落成、迎娶或归宁时,陈家人都会把这种匾在私宅的照壁上挂几日,图个喜庆。大忠祠内也有一块类似的挂匾,取词“鸿福”,据说质地是紫檀,平日里安放在大忠祠东厢房的一个犄角旮旯里,与那些室内存放的历代皇家所赐的字画、绵帛和器物相比,这牌匾实在是太不起眼了。“鸿福”乃“大难不死,必有鸿福”之意会,是为了昭告宗室后人永志不忘“壬午之难”所揭示的春秋大义和奶祖芮娘悲天悯人的胸怀,族内人对此心照不宣。每年祭祀祖先时悬挂于祖堂正南的影壁墙上,作为仪式的点缀仪式,同时希冀新的一年里陈氏世家在列祖恩德的庇佑下“鸿运当头天关照”。
围绕祭祖的话题,祖母讲过一段插曲。清末民初开始,走出去的族人越来越多,而回归者几乎寥寥。1925年,祖母出嫁前最后一次参加春节祭拜,已是盛况不再。虽有家道中落之端倪,但族人依旧衣着绸缎精工制作的礼服成礼,决不含糊。舅爷爷陈嗣长早年“闯关东”,几番漂泊后卜居齐齐哈尔,迫于生计很少回乡过年,在邮回蓬莱的拜年家书的起始段落都会写上“遥思为祭,守礼修己不周”的字句,以寄乡愁,并表达自己不能遵制亲祭祖先的愧疚。祖母在回信时总以“心敬如在,祖上有感”这样的话语来宽慰他。

伯父张绍宽“过百岁”时的全家合影,1935年6月摄于蓬莱。右一是祖母陈秀娟(怀中婴儿是伯父张绍宽),右二(站立者)是祖母之弟陈嗣长,中为祖母的姐姐浦陈氏(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浦克之母),左一为陈嗣长妻(姓氏不详),左二为陈嗣长的长子陈志群。
为了遮人耳目留住这块挂匾,祖母用我当年做夹克服时裁剪剩下来的咖啡色灯芯绒布头,拼接缝制了一个布袋套在匾上,看着像个坐垫,但她从不让任何人的屁股沾一下,放在她卧室的炕头柜最里端。每年寒冬来临,祖母把改头换面的挂匾放在棉被上,再放上镂雕着花草纹饰的椭圆形铜手炉,烘烤着她那已不太有活力的双手。我想,这承载家族记忆的挂匾和铜手炉里忽明忽暗的炭火,一定能给迟暮之年的祖母带来精神和肉体上双重的温暖。
我上小学时,大忠祠的祖堂已改造成紫荆山街道武霖村机磨坊,祭台处的地面上被挖出一条5米长、不足1米宽、1米多深的地沟,以确保碾米机和磨面机吐出的米面能准确无误地落入面袋中,镶嵌在四壁和廊道的勒碑已是千疮百孔,发动机的运转让整栋建筑一年四季都在颤抖,满屋充斥着柴油的气味,镂空的窗户上布满了夹杂着面粉的灰尘。祖母从来不让我拿着粮食去这里加工米面,而是去邻近的西关村机磨坊。
大忠祠的南墙正冲着影壁的地方开着“月亮”耳门,走进去,就是早已混居着周遭村民的陈家老宅。那时老宅业已充公,庭院里的杂草没过膝盖,瓦砾、碎石散落四处,这就是祖母再也回不去的娘家。上世纪90年代,连同大忠祠祖堂在内的相关建筑群落因旧城改造的需要被开发商铲平,只有这块幸存下来的挂匾成为见证大忠祠史诗般历程的片羽吉光。
有形易灭,无形永生。无论文明的证物是否还敛迹于历史的深处,大忠祠所寄寓的“忠义为道,至诚许国”思想,都在赓续且丰盈着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和浩然正气,这既是陈家人的生命之光,又是蓬莱人的不朽魂脉,是永驻人心的精神丰碑。
伯父张绍宽曾告诉我:“我曾问我母,我有这么多的姨,哪一个较亲?我母理解我的提问,意为老去后怎么报丧。我母说,我是城里陈家最后一人,亲友中已无了解我的人。意思是,后事都不重要了。”(张世峰)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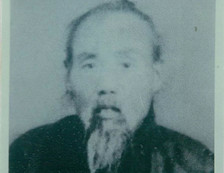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