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人口中所说的鲅鱼,生物学的名字叫蓝点马鲛。清代郝懿行在《记海错》中对蓝点马鲛(鲅鱼)记载如下:鲅鱼,身长而圆,状如织梭,肉厚刺少,味极鲜美。其色青黑,背有蓝点,故名蓝点马鲛。春末夏初,渔人网得之,市上多售,为海错中上品。

胶东的烟威渔场,是以烟台为中心,威海、莱州为两翼的全国性大渔场。烟威地区春天的鲅鱼汛,捕获时间从每年的阳历四月二十日左右开始,到六月十日左右结束,历时大约一个半月。捕获范围从威海最东边的成山头到牟平养马岛,从烟台市区到蓬莱长岛一线,从黄县(今龙口市)掖县(今莱州市)直达莱州湾乃至渤海湾深处。捕获的线路自东向西挪移,威海见鱼最早,掖县见鱼最晚,早晚相隔十天到半个月左右。
繁星数点芝罘湾
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东南自江苏的东海、赣榆,山东的日照、胶州;北边从辽宁的葫芦岛、盖县,河北的黄骅、沧州,山东的东营、滨州,每到春季谷雨节气前后,各式各样来自各省的渔船云集烟台芝罘湾外,赶春天的鲅鱼汛。借用蓬莱老作家陈鹏先生的两句话形容,那时的芝罘湾,真是“日出千杆旗,月落万盏灯”,盛况空前,一时无两。
当春鲅鱼从威海方向过来时,集合在芝罘湾的上千条渔船开足马力,纷纷出港。鲅鱼一夜西行,天将明时,集群在海水上层觅食。所以,要赶春天的鲅鱼汛,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都是在东方微明时撒网。这样,渔船就要在午夜两三点启航,经过两三个小时的航程,到达预定的海域。启航时,每艘渔船都亮起桅灯和角灯,与天上的繁星交相辉映。天空满天星斗,海里条条银龙,映照着芝罘湾如同龙宫贝阙一般。渔船一条接一条,一串连一串,按照头天晚上议定好的顺序,前船接后船,如雁阵般向深邃无边的大海驶去。
东方一露鱼肚白,渔网就纷纷撒到大海里。网的浮力大,白色的网漂都露在水面上。远远看去,鱼群来了,鱼群撞网上了,只见原先撒成一条直线的网漂凹进去一个大半圆圈。船老大沿着网道行船,来回巡视着鱼情。这左一个大半圆圈,右一个大半圆圈,都是一群一群撞上网的鲅鱼。有的鲅鱼紧贴在水面窜行,正好卡在了浮漂下面。站在船上,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青黑色的鲅鱼脊背在碧蓝的海水中闪着银光。这样的好潮头,哪一个打渔人不心花怒放呢?
我父亲出海经验丰富,遇事肯动脑筋。放完一网东方更亮了,再放漂网,就捕不到几条鲅鱼了,渔船纷纷回港。这时才刚到半上午,我父亲就琢磨:早上东方亮,鲅鱼起水在上层,会不会太阳出来后,鲅鱼就潜入水底了呢?说干就干,父亲马上把一船漂网改装成底网。预先估计出网的浮力,在网脚处每隔一米夹上一个陶坠。别的船只纷纷归航了,我们家的船又下了一次底网。好家伙!一条鲅鱼没捕着,却鬼使神差撞到海怪(大寄居蟹)窝里去了。这一网,足足网上了四五百斤大海怪。那时的海怪不值钱,块儿八毛一斤。父亲挑了几十个又大又肥的,砸碎海怪壳,煮了满满一不锈钢盆。正午时分,瓦蓝瓦蓝的天上没有一丝云彩,海上一丝风也没有,淡蓝色的海水没有一丝波纹。我们抛下锚,熄灭发动机,几个人围坐在一起,一瓶老烧酒,天为席,船为桌,悠哉游哉地饕餮了这一大盆大螯清甜无比、肉身香美异常的大海怪。如果换在现在,这一大盆大海怪,没有个千儿八百的,还真买不下来呢!
就这样打道回府,终究有些不甘心。吃饱喝足,善于琢磨事的父亲又把网脚的陶坠每隔两三米摘下一个,让底网变成悬在海中半沉半浮状态。这一招可真灵,一网下去,收获的鲅鱼几乎和早上撒东方亮那一网一样多。两网加在一起,足有上千斤的产量。归航到芝罘湾码头,已是黄昏。同村的船老大纷纷过来打探消息,面对惊羡不已的乡亲们,父亲毫不保留,把自己“发明”的新捕鱼方法传授给大伙。因为打渔人都明白,“行船走马三分险”,在苍茫的大海上,只有互帮互助、倾心与人相交,才是战胜一切意外与困难的法宝。
一轮明月高山前
经过二十余天“人追鱼”的鏖战,鲅鱼大部队已经转向西行。这时候,每条船每天的产量只能维持在一两百斤。船老大们一合计,纷纷起锚调头向西,挺进渤海湾深处,追赶鲅鱼大部队去了。我们从芝罘岛东口码头起锚,经过近十个小时的长途航行,终于在傍晚之前赶到了位于渤海深处的高山猴矶海域。
鲅鱼的习性是早晚浮出海面觅食。日头将要落山,满天的云霞把海水染成五光十色,金一道,紫一道,黄一道,绿一道,蓝一道。船头西南方向的猴矶岛,恰似一面敦重浑厚的扁圆形战鼓;船头西北方向的高山岛,斧砍刀劈般的悬崖直插入海,三角形的岛屿被晚霞映成一面红彤彤的战旗。
父亲端详着两岛之间的海况:一股浑黄的流水在海面泛起,这正是鲅鱼起水的最佳时机。父亲手搭凉棚,如一员临阵的将军,迅速调整好船行方向,匀速放慢发动机马力,负责下网的早就各就各位,只听一声“下网!”下网脚的拾起网脚,抡圆胳膊,网脚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弧线,“歘,歘,歘”网坠均匀地击打着海面,溅起一朵朵银白色的莲花,宛如凌波的精灵舞动着优美的身姿。下网浮的用一根光滑的长竹竿倚在大腿外侧,利用船行惯力,网浮犹如一条银线般顺着船舷,蜿蜒而下。父亲站在舵旁,两条腿夹紧舵杆,一只手牵引着发动机引线,掌控着船行航速,另一只手还不忘卷一只老旱烟棒。“刺啦”一声,火苗升起,一股青蓝的烟柱从父亲口腔喷出。透过烟雾,父亲的眼睛如鹰隼一般注视着附近的海况。这时,回首向船后一望,呵!一条长长的浮漂线,像界尺画过一样,又直又长,舒舒展展,平铺在半海瑟瑟半海红的海面上。
一船网下到海里后,停船,停发动机,做晚饭吃。渔船、渔网被海流拉着向西行。近处,标识各家渔网的红色芒子旗慢慢变灰;远处,搭伴一起夜渔的船只纷纷亮起了桅灯、角灯。一轮大月亮上来了,初夏的夜空碧蓝碧蓝,海上没有一丝风,仅有的几十颗星星散落在周天,有红的、蓝的、黄的、白的。这样温暖和煦的初夏夜,家里的洋槐树肯定正在努力喷吐着芬芳。猛地一抬头,猴矶岛已经移到了船的东南,岛顶驻军的灯塔,忽一明,忽一暗;高山岛已经移到了船的东北,一轮明月正挂在高山岛前。月,正圆而明亮,岛,三角而黝黑;这一正圆一三角,一极明一极暗,一上浮于九霄之外的青天,一扎根在碧波无垠的大海,任凭是多么高明的画家,也绝对构思不出如此壮美的自然画卷。
父亲吧嗒着老旱烟,一声不出,眯缝着眼,可能在小憩。我们渔家把等鱼儿上网这段时间称为“捂”,一直“捂”到晚上九点多钟,月上中天,开始起网。网头上,就有一串闪着银光的鲅鱼。一条一条鲅鱼,腰板挺得溜直。有的鲅鱼扎进网眼里肯定是挣扎了一番,鱼嘴张得老大。亮晶晶的鱼眼映着皎洁的月光,浑然是两粒墨玉。青白色带着蓝点的鱼身像一把刚被干将、莫邪从熔炉里淬炼出来的宝剑一样,凛凛放着寒光。网上的鲅鱼越来越密,越来越稠,刚从网上摘下的鲅鱼,清冷而浓重的鱼腥味直钻人的鼻孔。这样的好鱼汛,几年也不一定能赶上这么一次。从半夜九点多,一边起网一边摘鱼,直忙活到将近凌晨一点,才将这近两千斤鲅鱼从网上一条一条摘干净。
线江头上搬刀岔
大海是神奇的。陆地上有奔流不息的大江大河,大海里也有。在风平浪静的天气里,很容易观察到大海里的江河。船在海中行,忽然前方横着一条宽阔的玉带。这条玉带略高于四周海面,玉带里,海水的颜色与周围海水迥然不同。如果四周的海水是碧蓝的,那这条玉带的颜色或是棕黄或是墨绿或是靛青。就算是无风天,这条玉带也是细浪粼粼。略微有点风,玉带里就绽放出一簇一簇白浪花。这条条玉带就是大海里的江。蓬莱和长岛之间的海域有无数条或大或小或长或短的江,最大的江有两条,靠长岛近的那条叫线江,靠蓬莱近的那条叫沿圈江。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蓬莱与长岛大规模扩大扇贝养殖面积。县、乡镇、村、个人纷纷兴办养殖厂,蓬莱和长岛之间的海域几乎全部被占据。从陆地往海里望,一溜几十里,全是扇贝养殖架子。蓬莱的渔民失去了赖以为生的渔场,只好辗转到渤海湾深处进行撒网作业。渔船出一次海,光花费在跑路上的时间就长达十六七个小时,二十马力以下的小渔船根本不敢远航,渔民改行的改行,另谋出路的另谋出路。
到了每年的鲅鱼汛期,这些残存的二十马力以下的小渔船,为了生计,只能到线江头、沿圈江头搬刀岔。何为搬刀岔?过去大集体时代,生产队养大牲畜,要把成捆的玉米秸用铡刀铡成一小段一小段,这个活叫搬刀岔。线江头和沿圈江头四周全是扇贝养殖架子,只因江头水深流急,栽不下养殖架子,所以空出一块长三四千米,宽四五百米的地带。渔民把一船网,拆解成若干个小段,就在这窄小如螺蛳壳的江头上赶鲅鱼汛。狭窄的线江头,密密麻麻聚集着一两百条渔船,不是你家的船把我家的渔网撕了个大洞,就是我家下的渔网骑到了你家下的渔网上面,渔网与渔网搅成了一个蛋,乱成了一团麻,更惊心动魄的是,江头前后左右的扇贝架子犹如铜墙铁壁一般,流水风向稍微把握不准,渔网就贴扇贝架子上去了,霎时间,全部被海流卷入海底。鲅鱼一条没捕到,却落了个血本无归。
搬刀岔这个活计,就如拼命一般,抢时间、拼体力、耗心智。往年赶鲅鱼汛,渔场广阔,可以驰骋整个大海,一船网两三千米长,南北一字撒下去,威风又敞亮;现在线江头搬刀岔,完全没有了当年赶鲅鱼汛的悠然与自在,生生把人和船折磨成了团团乱转的齿轮,无时无刻不在提防意外与突发情况的出现。以明月、繁星、小岛为背景的赶鲅鱼汛,带着多少的闲适与诗意,收获的是丰收和喜悦;以江流暗涌四面楚歌的线江头为背景的赶鲅鱼汛,充满了为生存的奔忙与无奈,渲染着违背大自然规律发展的狂躁与凌乱。
大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不遵循规则的活动,如今,野蛮掠夺式发展的海水养殖终于成了“明日黄花”,一片片广阔清明的大海终于又还给了胶东沿岸的广大渔民。经过国家二十几年的休渔政策,渤海湾的鲅鱼汛逐渐又形成了规模,但愿在不久的将来,芝罘湾依旧能恢复“日出千杆旗,月落万盏灯”的盛景!(李心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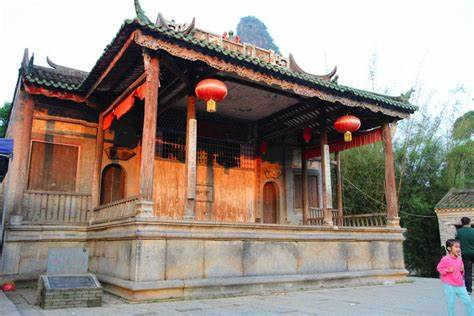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