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老市区三面环山,一面临海,靠海而修的许多街道,常据自然环境,在街名中冠以“海”字。如海岸路、海岸街、海岸巷、海滨里、海东街、海坝巷、望海街、后海崖街、北海里等。然而,旧时有这么一条街,同样依海而建,居民又多是码头劳工,海味十足,街名却没海字,俗称光棍衖(同“巷”)子。对于这条街巷来历,《老烟台街巷》一书中这样记载——
光棍衖子:位于现北大西街中段路北,北起原后海崖街,南至北大西街,长280米。始建于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前后,因原巷内多簇居码头独身工人,故始得名光棍衖子,后因巷名不雅,于1932年改名光国衖子。1973年更名光国巷。
这条当年民间口头流传使用的老街巷,原始成因镌刻了时代烙印,记录着烟台开埠以来码头劳工的一段沉重历史。
烟台开埠后,进出口货物陡增
烟台港原是一处天然港湾,自古就受到人们重视。至元明清,更是漕运帆船经常利用的避风港。晚清时期,随着海上贸易发展,始有少数外籍及外省船帮汇集此地中转货物。贸易量尽管很少,其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却引起西方列强的觊觎。英国驻烟领事馆《1865烟台贸易报告》中,有这样的表述:“在《天津条约》签订之前,烟台的贸易已表明它是一个重要之地,人们已经充分地知晓这一点,奇怪的是没有一个英国商人特别提出在条约里规定开放烟台的要求。”
有资料显示,早在1842年,据中英签订的《江宁条约》(即《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后,已有少数外籍帆船在烟台沿海登陆贩私。1861年烟台港口开放后,那些窥探已久的外籍帆船、轮船,满载货物竞相驶来。仅在1863年的9个月里,就有674艘次外国船舶进出烟台港,总吨位20余万吨。此后逐年上升。进出口货物数量的迅猛增加,使烟台港很快成为“整个中国北方货物集散地”。

1911年的烟台东海关货场(今太平湾码头)资料图
在洋货大量输入的同时,土货也开始通过烟台港外流。出口土货中的绝大多数属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其品种也在逐年增加。据不完全统计,1864年至1867年,自烟台港流向国外的土货达951936担,流向国内其它口岸的达5485568担。其数量虽然不扺洋货进口量,却远远超过了港口开放之前的土货出口量。
短短几年内,如此陡增的进出口货物,使得烟台港这处基本处于原始状态的天然港湾,其装卸过程格外复杂繁重。
缺少水工设施,装卸劳工数量庞大
开埠初期的烟台港,人工码头建设缓慢,更无配套机械设备,基本维持芝罘湾的自然状况。沿芝罘湾周边,没有任何可供停靠船舶上下旅客和装卸货物的水工建筑物。所谓码头,就是连接潮间带的自然岸滩。
由于港区南岸同样为浅滩构成,载重稍大的船只临港,必须锚泊在离岸较远的深水区,装卸货物须经多道工序才能完成。基本程序是:先将大船货物卸装到舢板,由舢板驳运至浅水滩,再由装卸苦力涉水将货物搬运至陆地。装船则依此顺序逆向操作。1866年海关码头建成使用后,因码头全长仅257米,水深不足5米,只能靠泊约500吨的船只。由于泊位有限,可直接泊靠岸壁进行装卸的船只数量并不多,当时还可基本满足需要。随着造船技术的进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千吨级以上船舶进出港口已成为常态。没有千吨级码头,这些船根本无法靠岸卸货,仍需锚泊深水区进行过驳作业。枯潮时,有些地方还要经过岸滩涉水搬运。
随着港口贸易量增长,从事装卸的劳工人数有增无减。尤其在烟台港开办客运业务后,又增加了驳运旅客、搬送行李的业务,进一步抬升用工数量。
1921年人工港池建成后,减轻了风浪对旅客上下船的影响,但由于建港工程中没有考虑客运设施,客运船只还是不能直接靠泊码头,旅客上下船仍需大量舢板驳运。随着客运规模的发展,在烟台港口从事装卸劳力的数量逐年递增。仅从舢板和舢板工的数量看,1891年约有舢板1200只,工人2400人;到1901年,港区舢板已达1700只,摇橹工人3400人,约占全市从业人口的7%。这还不包括专门从事装卸的劳工约5000人。
这种客运数量与配套设施不相称的状况,导致流向港口的廉价劳力增长速度高于港口装卸产业下游的各行各业。与当时港埠已有行业相比,市区内从事装卸、搬运的人口数量最大、增速最快,至1891年,占全市从业人口的比例升至56%。
每年数十万吨货物,多靠各类劳工背扛转运
由于烟台港缺乏较大靠泊能力的码头和必要的装卸机械,装卸作业必须使用舢板驳运,上岸或登船的货物,还靠人力扛、抬码垛或入船舱。这些港务劳工按具体工种被称为“摇舢板的”“扛包的”“背客的”“打现的”……
“摇舢板的”,多是几个人合伙买只小木船,通过帮头揽活,从事商船与海边之间的运输。
关于当年舢板工人的工作场面,1901年春来烟的美国长老会牧师亚瑟·朱德森·布朗留下这样一节记述:当我乘坐着从朝鲜来的轮船靠近烟台时,岸上美丽的景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海面水波不兴,在春天明媚的阳光下熠熠生辉……港口挤满了名为舢板的船只,这种船又宽,行驶又不灵活,上面站着精力旺盛的大个子中国人。船夫在边上摇着橹,靠近轮船,用钩篙钩住轮船的船舷,像猴子一样机敏地爬上长篙,跳到大船甲板上,然后就开始做起交易来。争着拉客的嘈杂声就像尼亚加拉乘马出游的人群那样喧哗……
从这位牧师的记述中,我们似乎已经触及舢板工人的艰辛。
“扛包的”(也称扛袋的),是指在深水区将商船载货搬运到舢板,越过浅水区后,再由舢板搬运至岸的装卸行当(装船则反向操作)。这里所说的装卸,全凭人力扛、背、抬、拖等方式。二三百斤重的货件,也是由一人背驮肩扛,再大些的则由2~8人结合移动。这些扛包的所谓装备就是一块蓝布头巾、一把手钩,负重踏着狭窄桥板,往返搬运各种货物。每当装卸货物时,桥板一头搁在沙滩上,另一头搭在驳运舢板上,距离稍远时,中间还可添几个桥凳支撑。桥板宽约半米,节节相联,形成一人可行的独木桥。人负重其上,桥板上下颤抖,这就要求人的脚步与桥板颤动必须同步,俗称“走上点”。此时若双脚配合不好,或前后人的脚步协调不一致,很容易连人带货被弹下桥板落海。搬运劳工经常是背驮大包,排着一溜长队,踩着桥板弹跳节律,如蚂蚁搬家一样上船下船。
据1867年的统计,当年进口货物16.06万吨,出口货物16.43万吨,平均每天进出口货物达900余吨。这时海关码头刚建成使用一年,岸上只有一架负荷5吨的固定吊杆。绝大部分货物是通过劳工们辛苦背扛转运的。
“背客的”,是指由陆地将旅客或行李来回背向舢板的行当,在人工港池成形之前,也是客运过程中一项不可缺少的环节。
“打现的”,是指那些无帮派等候临招的散工。他们常常“拥集码头,临时高呼,应声可即”。这类工人的收入没有保障 ,是码头工人中最穷困的,实际上就是些无业游民。
帮派众多,苦难单身劳工聚居成巷
自烟台开埠起,码头装卸就处于无专门管理机构的散乱状态,他们多是自发结成帮派组织,通过各帮头从洋行、商行老板、掌柜那里揽活,挣得费用维持生活。即使是正常从事装卸的劳工,收入也很不稳定。每装卸一条船的佣金,经货主、商行、把头等层层克扣,所剩有限。这也使烟台港的装卸劳力价格比较其他港口相对低廉。
大批装卸劳工因收人极低,很难维持正常家庭生活。许多装卸劳工无力组建家庭,开埠初期只能借助工棚搭伙聚居。后来随大小帮派自发组合成形,逐渐与组织海上航运的中外船行、商行沟通联系,形成相对稳定的雇佣关系。为方便生产调动,多数码头苦力帮派集体包租住所,其居住地址被称为“伙房”。所谓伙房就是集体宿舍,通常是数间通畅,并无陈设,筑一大炕或席地搭草铺即可,这类伙房在日寇占领烟台之前,散布于全市多条街巷。
1936年8月,烟台当地的《东海日报》曾刊文简介当时码头劳工隶属、居住情况。
招商局隶属三帮:驳船(摇舢板的)伙房在德胜街,伙计20余人,把头系福山县尚孝福。装卸伙房同在德胜街,伙计20余人,把头系潍县梁剑本。卸枯潮帮伙房在小太平街,伙计20余人,把头系文登县侯贵田。直辖三帮:驳船伙房在棋盘街,伙计10余人,把头系牟平县蔡国珠。装卸伙房在会英街,伙计20余人,把头系文登县曲云财。
政记所辖三帮:驳船伙房在棋盘街,伙计60余人,把头系黄县王喜刚。装卸伙房在德胜街,伙计30余人,把头系潍县张瑞麟。卸枯潮伙房与招商局所辖系一帮。
此外还有茂记所辖三帮、太古所辖三帮、裕记东所辖三帮、非商行隶属的高家伙房、蔡家伙房等。搬运行李的老孔帮、卢家帮,专事摆渡旅客的老帮、海阳帮,以及扛袋帮、小车帮等若干散居帮派。
散居形式由来已久。开埠之初,离乡农民移聚海港务工,人地两生,难寻稳定栖身场所,多是乡亲结伙散居海港附近。始建于1900年前后的“光棍衖子”,就是因巷内多簇居码头独身劳工,成为坊间口头俗称。
当年街巷北口临海,贫困的单身劳工,或就近搭建窝棚,或群租陋室。数十年间,随港口贸易发展、渔业渐兴,此地新建各类住所增多,并迁入数家商户,逐渐形成长近300米的街巷。而在此居住的码头独身劳工却有增无减,其街名也借风延俗,仍称光棍衖子。至1932年,才改为光国衖子。1973年更名光国巷。
这种记述烟台码头劳工居住环境的报道,见证了这样一段史实:烟台自1861年开埠至1936年,历经改朝换代、社会变革,前后70多年间,身处港口从事装卸的劳工,生活状况依然贫苦。这些从农村流入城镇的青壮年劳动人口,尽管身份发生变化,脱离农业生产,由农民变为市民,其社会地位没有上升,承受的苦难没有减少,社会阶层固化的现实,迫使他们世代难出寒门。码头劳工这种艰难处境,一直延续至1945年烟台第一次解放前夕。
在烟台开埠后的数十年间,这个衣衫褴褛、组织散乱的庞大码头劳工群体,成为烟台历史上的第一支产业工人队伍。他们汰老续新,艰苦劳作,以笨重原始的劳动方式,维持了烟台港口的正常运转,为新兴海港城市多个行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宋世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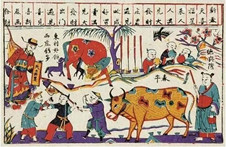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