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女婿和丈人的关系,在我的家乡牟平有这样一句俗语:“新鞤(bāng,古同“帮”)靴不换,新丈人爹不换。”这个“鞤”是什么东西?年轻人听来会莫名其妙,其实,它就是一种用鲜猪皮做的简易鞋,现在70岁以上的农村人大多都见过甚至穿过。

猪皮鞤资料图 文图无关
相比于鞋匠做鞋,猪皮鞤的制作要简单得多。
像我们这种男孩子多的家庭,冬天买不起那么多棉鞋,都是由爹爹动手给我们每人割(方言音ga)一双猪皮鞤。割鞤的猪皮只需刮掉里面的油脂而无需去毛,根据每个人脚板的大小,将猪皮裁成方头形状的长条,再对折成鞋筒状,使其结合面恰好处于脚背的位置。而后,将前后开衩的部分上翻捏合在一起,捏合面都用大钢针穿上麻绳缝得严严实实。针脚缝得不匀称也不打紧,因有猪毛挡着,也看不出个孬好来。
猪皮鞤毛在外,黑乎乎、毛茸茸,给人一种怪模怪样的感觉。用现在的话来说,有点“呆萌”吧。鞤里面楦进细碎的玉米皮、稻草叶或者羊胡子草之类的干草,暖和和、软绵绵的。虽然外表看起来不耐看,穿在脚上却很舒服自在。说到这儿,你就明白“新鞤靴不换,新丈人爹不换”这俗语什么意思了吧。
一双猪皮鞤通常能穿三年。穿过了一个冬季,就把它挂在闲屋的房梁上,过些日子就风干得“梆梆硬”了。等到了下一个冬天,用水泡软了再穿。风干后的猪皮鞤皱皱巴巴,模样更难看,因此形容某个人长得很磕碜,牟平话会说他长得和只“干干鞤”一样。
我12岁那年冬天,爹爹给我缝了一双“坐头(小号)”猪皮鞤。里面楦上柔软的稻草叶,别提有多么暖和了。大冬天,同学们冻得直跺脚,我却舒服自在。猪皮鞤还有个好处就是不透水,和同学们在雪地里做游戏,他们的棉鞋都湿透了,我穿着猪皮鞤却滴水不进。这让那些男同学很羡慕我,也让我动辄就会炫耀一番。
当年,我们村小学设在村南的马神庙,全村一到四年级的孩子都在那里读书。学校有规定,每年冬天从“三九”到“四九”这段时间,教室里都要生炉子。我是班级的劳动委员,班主任指定我和另一个同学轮流看管炉子,其他人严禁乱动。
有一天吃过午饭,我早早来到学校,把炉子添上煤,捅旺后就坐着烤火。一个不小心,猪皮鞤碰到炉子上,立马就冒出一股毛发烧焦的味道。这一瞬间,我冒出个念头——烤一烤会不会好吃?
我立马从书包里找出削铅笔的小刀,把猪皮鞤护脚背的“鞤舌头”割下窄窄的一小条,平放到炉子盖上。一转眼的工夫,那条猪皮就“滋滋”地冒出油来,随之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香味。我挑弄着,三五个来回,不光把猪毛烙得没了踪影,猪皮也烙得焦黄焦黄。凭感觉猪皮确实是烙熟了,就丢进嘴里嚼了起来。哎呀!想不到是那么好吃,对于我这个常年吃地瓜干的孩子来说,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好的佳肴美味。
打那天开始,我就像“吃腥了嘴的猫”,瞅准机会就把“鞤舌头”割下一丁点儿烙熟了解解馋。随着“鞤舌头”越来越短,我好多次都默默地告诫自己,这是最后一次,一定不能再割了,继续下去鞤就没法穿了。可一旦肚子里的馋虫爬上来,又什么都忘了,忍不住又把小刀拿了出来。
一个星期过去了,“鞤舌头”越来越短,已经凹进去了。为了防止妈妈发现,我每天回家尽量不和她打照面,及早把鞤脱下来放到小门橱底下,换上双单鞋穿着,告诉妈妈说是穿鞤脚发烧。早上穿鞤走的时候,也总是找个角落脸朝着里面,或者故意把稻草耷拉在脚背上,快速离开家。
“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这个秘密还是被妈妈无意中发现了。爹爹一听,火冒到了屋顶,一把抓起我撂倒在他膝盖上,“噼里啪啦”一顿笤帚疙瘩,生生把笤帚都打散了,我的两个屁股蛋也都变成了“猴屁股”。
我在炕上趴了两天才撇拉着腿去上学,班主任孙老师在班会上把我的“光荣事迹”公布于众,直把同学们笑得东倒西歪。记得孙老师最后说了一句牟平俗语:“曲范林,就你这脸皮,割鞤也能穿三年。”(曲范林 口述 刘甲凡 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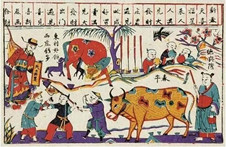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