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和挂谱
前不久,我去参观璜山书院民艺博物馆。在展馆里,一间复原的农村民居墙上挂着一件陈旧的挂谱,挂谱上面由上而下列着几排名字。同去的有研究家谱者讲,挂谱,农村百姓叫它“影”。“影”这个名称用得真好,寓意深刻又形象准确。挂谱“影”上面恭恭敬敬地列着一个家族故去的先人,他们曾经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每个人都拥有过精彩的人生,或建功立业,或文章天下,也有平凡如我辈的芸芸众生。他们虽然早已故去,远离了我们,但他们的名字却在一本本传承下来的谱书之中,他们的“影”挂在祠堂的高墙之上,临之在上,祭之如在。
挂谱,俗称家赏画、家影、祖影、谱轴等,是各个家族用于祭祀,记载着同宗共祖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脉络的图文,与家谱具有相同的功能。修家谱时,一个家族内,从逝去的先祖到刚出生的孩童都会入谱,而挂谱上只填写逝去的先人。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家谱和挂谱是以其特殊的形式记录家族的来源、迁徙、繁衍生息等过程的重要历史典籍。族之有谱,可以详里居、别支门、分宗派、明世系。中华民族历来有纂修家谱的优良传统,几乎每族每姓都修有家谱和挂谱,每个族姓大多建有自己的宗祠,又称家庙、祠堂或社房。宗祠是祭祀祖先的场所,挂谱就存放在宗祠里长年供奉。
珠玑村的宗祠
芝罘区珠玑村早年间是一个有一千多户的大村,村子里季、张、陈、王为四大姓氏,村里有七八座宗祠,或豪华气派,或矮小破旧,但每家宗祠都修有挂谱供桌和供器,院中植翠柏,高耸挺拔,郁郁葱葱。迈入宗祠,颇感庄重肃穆。
村子东头有申家宗祠。申氏家族在光绪年间出过两名举人,申宗海和申洪钧。申家宗祠雕梁画栋,恢弘大气,门前竖双斗旗杆,大门是八字粉墙,高大气派。双斗旗杆可不是有钱有权就可以随便竖的,而是皇上感念其功绩而御赐的,以表彰其功德,旗杆高高耸立,杆上有两个斗形装饰,寓其“才高八斗”之意。后来宗祠毁掉,旗杆和影壁也不见其踪迹,大院落也改作生产队的办公场所,只是那段残败的“八字粉墙”还在,我见过它衰败的样子,知道它曾有过辉煌的历史。
村西是我们张家的祠堂。史上我们张家也荣光过,出过两位文举、两位武举。清道光十一年,张省候中武举,官至莱州北海把总。道光十七年,张廷深中举人第八名,官至平荫县教谕。光绪十五年,张士魁中举人,光绪十七年,张殿鳌中武举。张氏宗祠也曾是青砖黛瓦、飞檐斗拱,八斗旗杆高耸巍峨。现在人们聊天时也常会说到“你们张家是竖过旗杆的”,这份荣耀还在延续着。后来,宗祠毁于战火。我小时候还见过张氏胡同里“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佛龛。门前的张家老井留存了下来,甘甜的井水滋润着张氏家族的一代又一代后人。
季家的宗祠和陈家的宗祠是建在一起的,在村子的中部,坐北朝南。季家的宗祠高大豪华,门楼高耸,五脊六兽,木雕彩绘,古朴精美,两扇黑漆大门上书写着行书对联“族推鲁望报享千秋,派衍姬宗勳垂两社”,横批是“百代昌盛”。听说季家出过高官,官大一级压人三等,季氏宗祠建在陈家的东面,足足高出了陈氏宗祠三尺还多。
陈氏宗祠在季氏宗祠的压迫之下更显低矮破败,一副寒酸的样子,但陈氏宗祠朱漆大门上镌刻着一副遒劲有力的颜体对联“忠厚传家流芳远,诗书继世锦泽长”,影响了陈氏家族一代又一代的后人。这两处宗祠后来归了集体,成了生产队的仓库和办公室。此外,还有梁家宗祠、刘家宗祠等都归了公,不是做了仓库就是成了生产队的办公室,后来全都成了瓦砾尘埃,无迹可寻了。
现在村里只有王家宗祠还留存着一段残破的石墙,茕茕孑立在荒草冷风中,诉说着前朝往事。
年节祭祀是大事
宗祠是家族供奉祭祀祖先的场所。每年按时把节(方言,遵守节期时间),全族人在尊长的带领下,恭敬地从宗祠里的大漆木匣中取出挂谱,挂在墙上;从神主楼里请出先祖的牌位,摆放在红木供桌上;前面的八仙供桌上摆好供品:猪头、全鱼和全鸡、光头大饽饽、应时水果和糕点。上香点烛,香火袅袅,缭绕其间,庄重肃穆。族人在尊长的主持下,按辈分依次跪拜,缅怀祖先恩德,祈求祖先庇佑。每年正月初一祭祀祖先,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祭祀活动,一直要祭拜到正月十五,才能将挂谱和牌位收好,存放在匣子里面,供品也收起来。

我曾听老辈人讲了一个陈氏宗祠的故事。陈氏族中的一支迁居莱山初家,老挂谱存放在珠玑宗祠,每年大年三十,他们族人吃过除夕饺子,就急三火四地从莱山赶到珠玑陈氏祠堂祭拜祖先。珠玑陈氏族人依仗支大人众,有些欺生,不是嫌人家来得太早,就是嫌人家来晚了,又是罚跪,又是罚香,终于惹恼了人家。转年腊月,月黑风高夜,几位胆大的后生翻墙入室,偷走了族谱,拿回初家悬挂祭祀……
这个传说在“文革”时不攻自破,陈氏挂谱从珠玑陈氏尊长家中被抄了出来。可能是迁走的那支族人来祭祀时就记下了先祖的名讳,又找画师新制了一个挂谱,四时八节取出来悬挂祭拜。年节时跑到供奉先祖的总祠祭祀确有其事,听老人讲,以前我们张氏族人在大年初一这天,要车马轿辇地去西牟村拜祖。珠玑这支张氏族人早先是从西牟村迁来,我们和西牟村张氏是同根同祖。每次祭拜仪式结束后,西牟村族人都会备上丰盛的大餐,招待远道而来的珠玑族人,一族人团结和睦,其乐融融。
冒着危险护谱书
新中国成立后,家庙宗祠全部归了公,成为集体财产,连名称也改为中性的“社房”,不那么有封建意味了。宗祠归了集体,挂谱则在各族尊长的家中客屋珍藏,逢年过节悬挂祭拜的仪式也传承延续了下来。
1947年,国民党军队占据烟台,孙氏宗祠遭到破坏,文物流失。《孙氏族谱》被我姥爷从火堆里抢了出来,抱回家珍藏,后又转由孙氏一支族人收藏。这族人尊长的后人,在“文革”时把族谱丢在家中顶棚上藏着,直到上世纪90年代翻修房屋时才记起。孙氏后人依靠这本老谱,重新续上了《孙氏族谱》,这段故事被孙家庄孙氏族人在重修《孙氏族谱》时记载在“大事记”中。
“文革”时,每年清明村里祭奠烈士。在福山文化部门工作的季德章老师因为被打成“右派”下放回村,在村里负责宣传工作,也成了我亦师亦友的同事。季老师能写会画,没有好的纸张,他就找出一件大挂谱,用纸把谱上的内容盖严,在上面写上村里为革命牺牲的十几位烈士的名字,两边是他用隶书写的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每到清明节,早上全村人集合在一起,祭祀先烈,虔诚地向烈士们鞠躬,缅怀烈士的丰功伟绩。人们并不知道,他们在祭拜烈士的同时,也祭祀了自己的列祖列宗。
族谱捐给图书馆
后来,祭祀仪式没有了,几件挂谱也无人问津。我高中毕业后回村工作,当了村里的保管员。我见到这几件挂谱,有些心痛,找来化肥袋子,把挂谱仔细包好,藏在仓库的角落里。挂谱被鼠啃虫蛀,饱受摧残,我也不知哪里是它们最好的归宿。正巧这时,我见烟台图书馆向全社会征集古籍善本文史资料,准备筹建“胶东文献库”,就请示村委领导,把这几件珍贵的挂谱捐送到烟台图书馆。2002年8月15日,我郑重地将珠玑村张、陈、王、季四大姓共五件挂谱捐赠给了烟台图书馆。

珠玑村是明洪武年间形成的一个自然村落,历史悠久,民风淳朴。张、王、陈、季是村里的四大姓,这五件挂谱就是这四大姓的族谱,其中季氏分东西两支,各修一谱。五件挂谱制作精美,尺幅宏大,宽有六尺,长有丈余,画面工笔重彩,古色古香,谱面书写蝇头小楷,记载内容脉络清晰,传承分明,庄重肃穆。几百年历史、几十代先祖,赫然在目,让人肃然起敬。五件挂谱对研究胶东地区早期先民的生息繁衍、宗族、姓氏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烟台市图书馆也极为重视,将其存放在古籍善本恒温室永久珍藏。烟台图书馆副馆长、谱版牒研究专家刘树伟先生肯定了五件挂谱的历史价值,特别对我们张氏挂谱给予赞美:“你们张氏的挂谱好,估计是清嘉庆年间所修,这么大的族谱保存得如此好,现在少见。”得到专家的肯定,我的心中有几分欣慰,这是我们几代珠玑子孙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在那天的日记里是这样写的:“今天将村里保管多年的五件挂谱捐给烟台图书馆,由图书馆整理揭裱,永久珍藏。我为列祖列宗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了却一份挂念和几多忧虑。列位先祖,对不起你们了……多年来,你们漂泊的灵魂,居无定所,东搬西藏,把你们搞得破烂不堪,灰头土脸,今天我给你们寻找到一个新的家——烟台图书馆。我小心地展开挂谱,轻轻地抚摸着你那憔悴的面容。再看你一眼,再看你一眼,恋恋不舍地将挂谱仔细地卷起来,抱起来送到来接你们的车上。再见了,列祖列宗。再见了,我的先人们。图书馆是你们新的归宿,是你们永久的家园。那里面山背海,碧水蓝天,有蕙风袅袅,花香淡淡,阵阵海浪伴你们长眠……”
现在,这五件挂谱珍藏在烟台图书馆四楼珍本恒温室,常有珠玑人去图书馆查询有关史料,图书馆工作人员都热情接待,取出挂谱让大家查询、记录、拍照。据悉,珠玑陈氏、王氏家族后人正在续修自己的家谱。
辛弃疾在《永遇乐》词中说:“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道出了家谱与民族精神一脉相承的重要性。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根在哪里?无论身在何方,不管漂泊多远,人们心中始终有着这种寻根的意识,正是这种寻根意识,进一步增强了民族的认同感、向心力和凝聚力。(张文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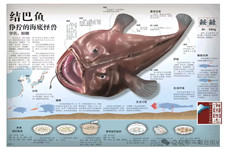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