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胶东半岛北部的烟台,濒临黄渤海,是我国北方有名的渔港之一。
过去,烟台一年四季大小鱼汛不断:每年立春前后,由对马海峡回游到渤海湾生儿育女的大对虾,成群结队地来到半岛东端成山头一带海域,一年的海上捕捞,就此拉开了序幕。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大群的花鱼(黄花鱼)蜂拥而至;谷雨前后,又到了用底网拉刀鱼(带鱼)的时候;立夏前后,成群而来的鲐鱼,标志着最大鱼汛期到来;秋分前后开始拉秋虾、鮱子鱼、大头鱼(雪鱼)和河豚鱼。
尽管捕捞工具落后,早年除永平公司等几家有对木壳汽排子(机轮渔船)外,都是木帆船。网具是用猪血加热浸泡过的棉线鱼网,最大鱼网长度也不足百米。但来烟台港卸鱼的渔船四季不断,尤其是鲐鱼捕捞季节,海沿上的鲐鱼堆成山,最高日产可达百万斤之多。
在陆上运输多赖大马车和大板车、更无冷冻和冷藏的年代,海产品加工成为烟台不可或缺的重要行业。
1918年8月,由总商会投资在北马路东部路北(现渔业公司东侧)建成占地面积5082平方米的当时最大的公利市场,老烟台人俗称“鱼市场”。这里的大小渔行最多时有一百多家,如鱼市场西侧,长仅有280米的海东街,就有大小渔行10家,坊称“渔行街”。后海崖街也有渔行近十家,人称“渔行一条街”。

现有据可查的渔行近70家,分布在北马路、东莱兴街、会西街、瀛州街、西莱兴街、后海崖街、海东街、会东街、海滨街、光国巷、裕顺巷、西河东崖和德泰巷。渔行加工制作的咸干鱼虾销往国外及国内各省市包括京津沪等大城市。
渔行的副产品也丰富了烟台市民的餐桌。春天的虾头鲜美可口营养丰富,几乎家家都用它熬大菜,用虾头磨成的虾头酱更是餐桌常客,鱼子炒韭菜是有名的传统鲁菜,鱼子炸酱面是烟台的名吃。
渔行的活儿,既苦又累,尤其是掐虾头、割鲐鱼、腌咸鱼、捞咸鱼,都是非常遭罪的体力活。
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外销的对虾要求是无头虾,需人工将虾头掐掉。对虾是甲壳海产品,身上的透明壳中含有一种名叫嘌呤的有机化合物,掐虾头的工人,长时间不停地接触对虾,多数人都会过敏,手指头被腐蚀得发肿破皮露出红肉,稍一碰触,钻心的疼痛。对虾捕捞期长达20多天,为了生计,再遭罪也得干下去。
最大的鲐鱼汛期来到时,大量的鲐鱼堆积在海沿上,那时尚未封盖的西南河北部东西两岸也都堆满了鲐鱼。
海产品质量的好坏,关键在一个“鲜”字,要抢“鲜”,就得有足够的人手。为了尽快招到割鱼工,各渔行不得不到大街小巷游说,吸引家庭妇女和无业青年加入。她们三五人结伴,来到渔行,几天下来就成了熟练工。挥动着凸月形的割鱼刀,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连续多日干下来,累得工人站起身都需他人拉一下,有的人累得在吃饭时竟含着饭就睡过去了。
后来随着渔船的更新,渔具的改进,海产品的捕捞量剧增,割鱼的队伍越来越大。公私合营前夕,政府将这部分人组织起来,成立割鱼队,清一色的娘子军,属大集体编制。
腌鱼、捞鱼更是渔行中苦不堪言的活儿。
腌鱼的池子是用洋灰(水泥)抹面,池子高于地面近1米,深入地下四五米,长宽因地制宜无定数,一般小的池子能腌一两万斤,当时最大的全兴义渔行,一池能腌五六万斤之多。
腌鱼时,两人抬着能盛二百多斤重、高约半米、棉槐条编的圆鱼筐,踮着小碎步,小跑着通过地面与池沿连接的桥板,把鱼倒在搭在池子上的木板上,加上盐(鱼与盐的比例为四比一),用木锨拌匀,推到池子里。
抬鱼、抬盐、拌鱼,如此连续不间断地干,直到数万斤的池子腌满。然后,在鱼的上面放上用棉槐条编成的大排子,排子上再压上数块重达二百多斤的大石条,数条壮汉忙乎一天,这项工作才得告一段落。
说起捞鱼的活儿,更是令人不寒而栗。
鱼腌好后,先搬除池子上压鱼的大石条和大排子,整齐地码放到池沿下面,以备下次使用。然后,一人下到鱼池里,用一种叫捞栳的工具(木柄,一端有圆形铁圈,圈内罩网),把池中的鱼捞进鱼筐里,一捞栳可盛三四十斤鱼。筐满后,两人抬走装车。
随着出池的腌鱼增多,为了防止上升鱼筐的鱼水流到身上,池中捞鱼人不得不戴上斗笠,穿上油衣油裤(类似于雨衣雨裤),在冰冷的池子中不停地挥动着捞栳。
随着腌鱼离池沿越来越深,两个提筐人握绳的双手越来越吃力,一池子几万斤鱼捞完后,双手发胀握不住拳头,累得精疲力尽,连说话都有气无力。
1956年公私合营,烟台成立了水产加工厂,各渔行都合并到加工厂的腌制车间,并成为车间的分散加工点,共计31个,烟台人俗称水产库,简称为水产一库、二库……直至三十一库。
上世纪60年代初,水产加工厂新建的理鱼车间和三千吨冷库及冷藏车间,先后投入使用。理鱼车间把新鲜的鱼整理、定量、装盘,再进行冷冻和急冻保鲜。陆路上开通的火车和冷藏车,也使离大海较远的内陆吃上了新鲜的鱼虾。落后的水产腌制工艺,逐渐被淘汰。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区的改造和道路拓宽,老鱼市场和水产库全部拆除,那些老渔行也消失得无踪影了。(祝明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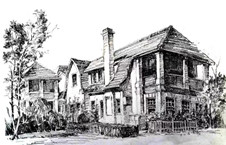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