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大褂、急救箱、听诊器、血压计,这是医生出诊的标配,但在我4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其中有3年,出诊包中还带了一样铁家伙———手榴弹。
上世纪60年代末,我毕业后分到了牟平养马岛,当上了一名海岛医生。岛上驻军多,民兵多,军事气氛紧张,两千多户居民过着半渔半农的生活。卫生院设在租赁的私人四合院里,有5名大夫。
岛上谁家有病人,都是请医问诊,往返取药送药是医生的事。岛里人叮嘱我,晚上出门要格外小心,因为夜里常有敌特打信号弹。但医生夜诊是家常便饭,走夜路在所难免。而且我年轻,更是首当其冲。

本文作者
那时,尽管有民兵来“叫医生”,但人家“管请不管送”,回去或是往返拿药就得单飞。一个人走在漆黑一团、林深草密的山道上,别说有敌情了,单是风吹树叶哗哗响,路旁野草瑟瑟摇,山间猫头鹰咴咴叫,就让人头皮发麻、后背发凉。
有天晚上,我被叫到孙家疃村出夜诊。完事后一个人踏上归途。那晚,月明如镜,月光洒在海面上,波光粼粼。突然,我发现海边有亮点在晃动。“什么东西?”我一下子紧张起来,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片刻冷静之后,我决定上前瞧个仔细。逐渐靠近目标时,赫然看到礁石下有人,而且都拿着手电筒。“坏了,是不是遇上敌特了?”我急忙一边隐蔽一边观察。看了半天,见这些人似乎只是弓着腰在礁石边寻找着什么,不太像特务。
于是我壮着胆子大喝一声:“干什么的?”“不干什么……俺是赶小海的。”听得出,被我这一吼,对方也吓得不轻。虚惊一场!
发生这件事以后,我就想,要是有把枪该多好,夜诊就再也不用怕了。于是,凭着医院与部队的亲密关系,我直接找到驻军代表孙政委:“政委,我各方面条件也够得上基干民兵了,能否发我一支枪,晚上出诊也好防身。”
孙政委笑着对我说:“配枪上级有严格规定,但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晚上一个人是不安全。这样吧,咱们找武装部长商议一下。”
武装部的孙部长听明来意,对我说:“小王院长,咱部里没有短枪,给你支步枪怎样?”我一听就摇头了:“步枪五尺多长,背在身上骑自行车不方便,再说晚上到患者家也挺瘆人的。”
部长又想了一会儿,说:“那就手榴弹吧!把它放在出诊包里,一旦有情况就拉弦尽量往远处扔,听到响声岛里驻军和民兵会立即赶到。”
就这样,我到武装部库房办理了手续,拎回了两颗手榴弹。一开始,还小心翼翼生怕弄响,经常从包里拿出来瞅瞅。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你别说,自打有了这“哼哈二将”,上山下海、进村入户、茫茫夜路,我心不慌了,底气足了,劲头更旺了!
我的秘密武器最终还是露了马脚。医院里除了会计是位老兵,能理解我,其他同事都避之唯恐不及。出于安全考虑,我一个人搬进了仓库住。3年里,我跑遍了海岛8个自然村,接出诊病人不计其数。这两颗手榴弹既是我的安全保障,也是忠诚战友,更是医院建设的见证者。
自1969年开始,在县卫生局和公社党委的支持下,我和其他同志一起跑县上,找市里,乘车、雇船、人抬、马拉,买来一车车木料、石材,筹来一船船钢筋、水泥,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盖起了新医院,结束了海岛缺医少药的历史。
1972年,我调到城关医院(宁海医院)任职。离岛前,我郑重地把两位“老伙计”交还了武装部。(王德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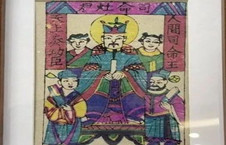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