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地处牟平区最东端的黄海岸边,那里有一条南北走向、与大海潮汐相通的天然港湾,当地人称之为东海。港湾西面,除了海滩,便是几千亩粮田。
四十多年前,每到秋天,从西伯利亚回到我国南方的大雁,或者是从这里的天空飞过,或者是在这里的庄稼地里歇脚。这些年年见面的大雁,当地人称它们为“老雁”。
这时,社员们都在田里忙着种小麦。当第一声雁叫传来,人们会情不自禁地停下手里的活儿,直起腰,久久地仰望着天空中南飞的雁阵。姑娘们更是手搭眼罩,痴痴地望着,直至看不见大雁的影子。生怕耽误了干活的生产队长,大声吆喝:“咋啦?都在家想女婿吗!”招来那些小青年的一片嬉笑声。
队长对姑娘们凶的那句“糙话”,是有来由的:有一年冬天,村里与巧莲姑娘相恋了三年的小伙儿都春牛和另外两名青年应征入伍了。送军的那天早晨,村前的老柳树下站满了人,欢送的锣鼓震天响。
就在春牛准备上车的时候,巧莲姑娘突然从人群中冲出来,伸手拽住了春牛的衣角,久久不肯松开。现场安静下来,所有的眼睛都盯着这对恋人。
对望半天,春牛轻轻握住巧莲姑娘的手,深情地说:“巧莲,等着俺,每年秋天,俺会让南飞的大雁把俺的立功喜报捎给你,看到了大雁,就是看到了俺……”巧莲扭过身,双手捂着脸抽泣起来。
从此,村里人每当见到大雁从天际飞过,总会与这一幕联系起来,年年不忘,年年相传。
当大雁飞临村庄上空,孩子们就欣喜若狂起来,他们昂着头追赶着天空中的雁阵,边跑边喊:“老雁、老雁,掉锅里哈(喝)面;老雁老雁你别走,快来俺家哈壶酒……”直至把大雁“送”出村庄。
孩子们说的哈面哈酒,并不是要请大雁的客,而是期盼着大雁能从天上掉下来,让母亲做一顿用大雁肉开卤的面条,让父亲就着大雁肉喝上一壶老酒。
当然,从来没有一只大雁无缘无故地从天上掉下来,相反,听到喊叫声的大雁会一鼓作气,飞得更快,更高,更远。
大雁落地,一般选在午后或黄昏。天空中突然传来隐约的雁鸣,只见从大海那边的长空悠悠飞来一群大雁。雁群呈“人”字型,越飞越近,领头雁可能是发现了大地上墨绿的麦田,接着,雁群变换队形,越飞越低,继而,上百只的大雁在麦田的上空盘旋起来。

这时,如果你隐藏在麦田近处的地沟里,当盘旋的雁群离地面丈余高的时候,你就会清晰地发现,一只只灰褐色的大雁羽毛润滑,体形健硕,身姿十分漂亮。
当雁群从头顶掠过时,耳边带过“呼呼”的响声。当盘旋的雁群离麦田有人那么高、头雁确认地面上没有危险的时候,雁群便在头雁的带领下,缓缓着陆,稳稳地站立在麦田里,高昂着头,收起双翅,抖落一身风尘。
有时候,一群大雁刚落地,紧接着又飞来另一群大雁。当这群新飞来的大雁发现下面的麦田里有自己的同伴时,知道平安无事,头雁一声令下,雁群即刻降落。
这时,麦田里的大雁见来了“客人”,会热情地向天伸着脖子呼应。就这样,大雁一群接着一群飞来,又一群接着一群降落。到太阳落山的时候,麦田里就会有几百只甚至上千只大雁汇聚在一起。隔远望去,夕阳下的雁群黑压压的一片,场景十分壮观。
大雁的警惕性很高,落地以后,头雁会在雁群周围布下道道岗哨。那些负责站岗放哨的大雁很是恪尽职守,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不换岗之前,它们不吃、不喝、不睡,一旦发现风吹草动,立即大声鸣叫示警。
大雁的嗅觉也是很灵敏的。一个赤手空拳的人在离雁群一百来步远的范围内,大雁多半不会在意的,但若是有人带着猎枪哪怕走在两里地之外,即使他将猎枪藏匿在草捆里,雁群都会随即警觉起来,似乎大雁对火药的气味异常敏感,一旦猎者向它们走来,它们就会大呼小叫,振翅起飞。
第二天早晨,在麦田里吃饱睡足了的大雁重整阵容,一群接着一群地披着朝霞,展翅踏上了新的征程。大雁宿过的麦田里,留下了一片片受伤的麦苗和满地的大雁屎。
庄稼人见了这场景,会一遍一遍地念叨:“麦苗不怕踩,就怕老雁逮(吃)。”意思是说,冬前停止生长的麦苗不怕踩踏,而让大雁吃过了的麦田,来年的小麦就会减产。
尽管庄稼人疼惜庄稼,可人们从来也不舍得伤害大雁,年年只盼大雁归,南飞的大雁已成为庄稼人心里割舍不下的念想。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乡亲们发现,在家乡的麦田里留宿的大雁一年比一年少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竟一只大雁也看不到了。想啊盼啊,三十多年过去了,至今也没能把大雁盼回来。
不知道大雁们都到哪里去了,我想对大雁说:大雁,回来吧,如今的家乡山美水美人更美,我们努力擦净天空,等你们来。(都兴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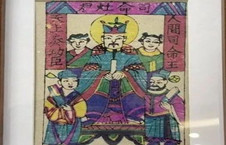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