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是农历一年中最末的一个月,是人们打理心情展望丰年的盘整期,对我来说,也是一年中最为闲适的时光。而赶腊月集,对我更像是一个放松心情的美事。
集市平常日子也有,但人并不多,腊月集就不同了,冬闲的农家人就有了大把的时间,如果再逢双休日和学校放寒假,那集市上就会人潮涌动,仿佛戏迷看大戏一般。
有的人平时不爱赶集,但到了腊月,却逢集必赶,“集溜子”说的就是这种人。
赶集的人不外乎两种:一是有明确的目标,心无旁骛,要买什么直接奔目标而去,谈好价钱买了就折返回家,不在集市上长时间逗留;还有一种人,赶集并非要真的买什么,而是随性而来,东瞅瞅西望望,满市场转悠,没有目的性,赶上中意的就买,人称“赶闲集”。
我平时不大愿赶集,一是由于现今的福山大集在上夼村附近的一个大坡上,不太方便;二是平时摊少人稀,人气不旺。但到了腊月,特别是放了寒假以后,我却一定要赶几个腊月集。一是门楼大集,二是福山大集,间或也到舒家集上转一转。
赶门楼集,因我老家是门楼镇的,打小随奶奶赶集的缘故。
小时候,腊月村里开了支,几个叔叔姑姑都会给奶奶一些钱。奶奶就会颠着小脚领我去赶门楼集。
集市离村子三四里路远,那时还没有岚柳墅大桥,需要踩着石头过杨家河(今称羊角河)。到了集上,奶奶会买几盅尖波螺。糖球最吸引我:一根竹签,叠罗汉似的串起颗颗被冰糖包裹的山楂果,冰糖晶莹剔透,果实红艳欲滴,红彤彤的,格外喜庆。我扯着奶奶的袄襟一路挤挤挨挨地奔了过去,挑那又大又红无虫眼的买上两串。

资料图
那时,桃酥可是人人想吃的稀罕玩意,奶奶这时也会狠狠心,到供销社买上油纸包着的核桃酥,小心翼翼地放到拐着的白条篓子里,怕油纸碎了,篓底下还用头巾垫上。一路上,我的心思全都在桃酥上,不时看看篓子。回到家后,奶奶掰一大块桃酥给我,看着我狼吞虎咽,她自己只吃点桃酥渣渣。剩下的,奶奶会放到大柜顶上或是挂到房梁上的篓子里,吓唬我说“吃多了烧心伤胃”。
这桃酥主要是用来正月出门的,放在篓子的最上面,出门临往回走时,口口声声告诉亲戚一定要留下桃酥,一个是假意要给,一个是真心不留,假意推辞一番,心里难免有一丝担心:可别真的留啊,真的留了,后面的门可就没法出了。
这样转了一圈下来,桃酥又原封不动转回来了,有时出完门回来,桃酥都稀碎了。
家中正月来客,就把桃酥拿出摆在小碟里待客。我们这些上不了桌的小孩,会不时挑起门帘瞅一瞅桌子上的桃酥,有的客人就会赏我们一块,家里的大人就一迭声地嗔怒“小孩子不懂事”。
门楼集是逢一、五赶集。
有一年记不清是腊月十一还是腊月十五,我们一家三口到门楼赶集。集上人山人海,三九天,很冷,大集旁边有家小饭店,门口支着一口大锅,煮着一锅汤,旁边挂着一副羊架。老板问:“来三碗羊肉汤吗?”我们三个都不吃羊肉,就让他给上三碗猪肉汤。老板答应得很痛快,不大一会儿,三大碗猪肉汤上来了,喝了一口,羊肉味,再喝一口,还是。最后我们才想起来,就门口那口锅,羊肉锅里放猪肉,能喝出猪肉味就出鬼了。
门楼的羊汤和淡水鱼远近有名,而我对这两样都不感冒,真不像门楼人。
千年古邑福山,集市的存在时间想必也很久远,虽几经搬迁,但辐射范围未受影响,逢集日,经常看到来自莱山和芝罘区的一帮老头儿老太太乘33路车结伴过来赶集,大包小卷地满载而归。
福山大集我一般是赶腊月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六这几个中后半程的集,一般是十点以后去,大多也没什么目标,主要是去感受腊月集市上过年的气氛。
卖门对子的地方是绕不过去的,红红的门对子不光看着喜庆,从上下句中也能看出人们对国家政策、美好生活的感谢和憧憬。烟花鞭炮摊位的生意不如从前了,而花鸟鱼市却人流不断。海鲜鱼市上,人们不再关注价钱,只挑那新鲜、个头大的鱼、虾、蟹成箱往家搬。炒货摊前,瓜子、花生都不愁卖,大锅炒的花生更是抢手。推着小车卖年糕的老人,脸上挂着笑容,半头晌不到,年糕箱就见底了,人们图的就是一个“年年高”的希冀。
熙来攘往的腊月集上,生活的变迁,节日的精彩,都在眼前一一展现。(刘宗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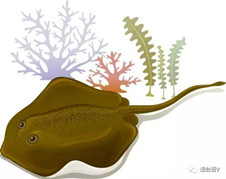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