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唱过好些童谣,有一首叫《小孩小孩要听话》:
小孩小孩要听话,你妈在家烀粑粑。
黄面粑粑给你爹,你爹推车下西洼;
黑面粑粑给你哥,你爹推车你哥拉;
红面粑粑给你姐,你姐有劲把鞋底纳;
穇子粑粑留给你,‘唰唰、唰唰’会说话。
家乡人管饼子叫粑粑,这里提到的黄面、黑面和红面,分别指的是苞米面、地瓜面和高粱面,穇子粑粑是什么,你知道吗?
合作化之前,我们村北有百余亩平展展的泊地,沁水河河床比这些地块高出好多,到了汛期河水常会漫过堤坝,受淹的地块就变成盐碱田了。盐碱田种不了玉米、大豆,穇子耐盐、抗碱、不怕涝,一场大水过后,三五天的工夫,穇子就又郁郁葱葱了。
种穇子,和种别的庄稼不一样。爷爷他们先在街口把土粪摊开,用二齿子或粪叉子捣得细细的,运到地里,一堆一堆分布开来,再把穇子种均匀地扬洒在土粪上,然后用手抄着土粪搅拌,直至均匀。播种时,老牛拉着木犁头前开沟,人随其后,脖子上挂个粪筐,走一步,抓一把混和了种子的土粪下地,紧跟着再踩上一脚。最好再跟着个孩子扫尾,拉着芦苇扎的草把子顺着垄沟拖一遍,播种就算完成了。

穇子分蘖性极强,其粗壮的秸秆能长到一米多高,从来也不会因大风而倒伏。到了抽穗的季节,直溜溜的秸秆顶端擎着5个或7个呈鸡爪状分布的穗子,一穗穗形如狗尾巴,所以我们也叫穇子“鸡爪子谷”。
除了盐碱田,在农田靠近路边的地头上,通常也会种点穇子。种在这里是有用意的:收获时节,刨下的玉米秸秆可以用穇子秸秆捆起来。更重要的是,家家都养牛,老牛经过地边时,瞅空就会拽上几口庄稼吃,唯独穇子它不敢动,因为穇子的叶芒带刺,它的舌头受不了。这也算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吧。
家乡还有句农谚叫“处暑三日无青穇”。此时,就要收割了,妈妈和奶奶们带着剋穗的方刀、麻袋、席子和条编大柴篓子,一大早就到了大田里,两亩地的穇子,她们一天的工夫就都把穗儿剋下来了,再用小毛驴驮到村南的打谷场上。三五个日头晒下来,爷爷他们“噼里啪啦”一顿连枷,再迎着风用木锨扬场,一堆土黄色的穇子粒儿就干干净净了。
穇子的产量不算低,正常年景亩产都在500斤以上,麦收后到秋收前,可补夏粮的不足。
穇子要上石磨磨出粉来。奶奶她们总是先用大磨眼儿粗粗地流下来,用簸箕扇出最粗粝的那一部分,接下去再用小磨眼儿细细地磨一遍。筛分面粉的马尾罗用最粗的那种,罗下的面粉用来烀穇子粑粑,罗上的糠皮用来喂猪和鸡鸭。
米糠筛分不细,烀出来的粑粑入口涩涩的,稍一咀嚼就会发出“唰唰”的声响,吞咽时则会剌得嗓子眼痒痒的,家乡因此有两句俗语:“河水年年淹西洼,穇子粑粑会说话”、“没吃过穇子粑粑不知道粗细,没上过高山不知道平地”。不过,穇子粑粑的味道还是香的。
合作化后,沁水河的堤坝加高了,涝洼田改造成了水稻田,从此不种穇子了。
1989年秋天,我带队在胜利油田孤岛施工,那里地处黄河入海口,放眼望去,全是无边无际的荒草地,密不透风的芦苇和水穇子长得一人多高。一刮秋风,水穇子的籽粒落到海边,厚厚的,一片连着一片。当地老百姓把这些水穇子粒儿捞回家,晒干后磨成粉,做成穇子粑,口感相当不错。但加工得再精细,穇子粑粑还是“会说话”。
而今,如果说有什么好饭食让我惦记的话,口感粗粝的穇子粑粑算是一种。(刘甲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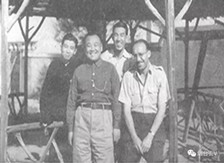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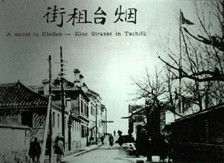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