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版《黄县志》卷一《建置志》有“大入城:在县北二十里,今其村名军营,城上有海渎祠,城西北有射圃。”
其注一云:大入谓大举兵入辽东。《元和志》言“伐辽东造此城,运粮船从此入”,亦可证。府旧志作“人”,误。《明统志》《通志》《县旧志》不误。
注二云:《县旧志》载:“司马懿伐新罗,筑此城以储粮。”按:汉魏时,无“新罗国”之名,此说固误。
究竟是“大人城”还是“大入城”?这个“城”又在哪里呢?
当是大人城而非大入城
清同治版《黄县志》认为黄县黄河营村(即军营)有古城,名字应为“大入城”而不是“大人城”。查《元和郡县图志》登州黄县条:“海渎祠,在县北二十四里大人城上。”《水经注图·汉东莱胶东二郡国图》云:“《元和志》司马懿伐辽东造大人城于登州西,运粮船从此入。”《新唐书》载“于是北输粟营州,东储粟古大人城”,朝鲜《三国史记》因之。清谢钟英补注《补三国疆域志补注》亦作“大人城”。
宋《太平寰宇记》(据光绪金陵书局版)起,始有“大入城”的说法:“大入故城,在县东北二十里。司马宣王伐辽东造此城。运粮船从此入今新罗、百济,往还常由于此。”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因之。综合看起来,笔者认为:“大入城”的说法出现较晚,系抄刻之误,是站不住脚的。
地理上大人城应在烟台芝罘岛
关于“古大人城”的地理位置,到清朝时即有永平府抚宁县、锦州锦县、登州黄县等观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9月第3期发表李效杰《“古大人城”与中古东亚的海上交通》一文,论证古大人城位于黄县的黄河营,仍然是牵强附会,未能形成定论。“大人城”究竟在哪儿,已经成了千古之谜。
唯一有价值的线索,是《册府元龟》中的记载:“海中古大人城,西去黄县二十三里,北至高丽四百七十里,地多甜水,山岛接连,贮纳军粮,此为尤便。”唐太宗采纳了建议,“于是自河南道运转米粮,水陆相继渡海,军粮皆贮此。”《册府元龟》卷489《邦计部·漕运》应该是唐代的第一手资料、原始证据,有别于后期编纂的地理文献,可信度较高。
千百年来,对“大人城”的研究,文史研究者一直是以现黄县城或者旧黄县县城为坐标的,并未跳出黄县境内,是故难以寻到大人城的踪迹。而查阅唐代黄县的疆域文献发现,唐贞观元年(627),废牟平、清阳两县,划清阳河以西之地归黄县。其时,黄县之东境与汉晋境域略同。清阳河即现在的烟台市的内夹河。1唐里约等于现在的450米,23唐里约合10.35公里,以夹河河口为圆心,10.35公里为半径寻找,目标指向了烟台市芝罘区芝罘岛。
芝罘岛由连岛沙坝与大陆相连,岛上为丘陵低山地形,主峰老爷山海拔298米,东西长约9公里,宽约0.5-1.8公里,是中国最大的、最典型的陆连岛。芝罘岛上也出产淡水。所以,同时符合在海中、黄县边境以东23唐里、距离辽东半岛470唐里、地多甜水、山岛接连五个条件的岛屿或者半岛,有且只有芝罘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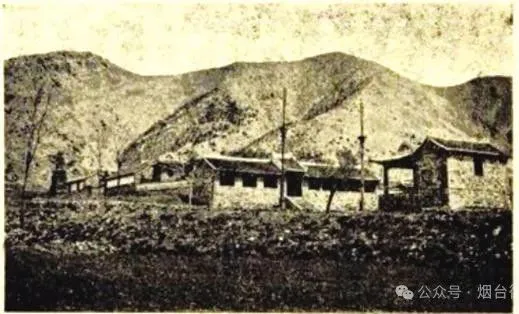
还需检测一下“北至高丽四百七十里”这个问题。以芝罘岛为圆心,以212.5公里为半径向北,也完全符合《册府元龟》的记载。
从军事和航运角度复盘大人城
芝罘岛是秦始皇东巡的终点,也最有可能是历代伐辽的补给地。
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刘彻遣使臣涉何出使属国朝鲜,朝鲜王拒受谕令,涉何杀死了朝鲜裨王长,并接受了为辽东(郡治襄平,今辽宁辽阳市)东部都尉的任命。朝鲜王怨恨涉何,发兵击杀涉何。是年秋,武帝下令招募死囚,分两路征讨朝鲜:一路是左将军荀彘率军从辽东出发由陆路出征;另一路是“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勃(渤)海,兵五万”。这五万“齐卒”,“入海已多败亡”,到了朝鲜连吃败仗,连死带逃,到决战时只剩下七千人了。楼船从齐的何地出海,史无明文,倒是汉武帝的叔叔、为了谋反整天研究地图的淮南王刘安留下了一句话:“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淮南子·时则训》),此为海路,可以到达扶桑。贯,穿过。这话的意思就是,从碣石山出发由海路到朝鲜,必须经过大人之国,进行补给——“大人之国”应该就是大人城的前身了。
建安十二年(207)五月,曹操率领大军准备出征辽东乌桓,不过由于是轻装突袭,这次征辽东没有海路出击的记载。曹魏太和六年(232),明帝遣汝南太守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从陆道,并攻辽东,无功而返。景初二年(238)三月到八月,司马懿伐公孙渊。《元和郡县图志》“司马宣王伐辽东,造此城”。“大人城”作为征辽补给地的地位确立。
贞观十五年(641)八月唐太宗欲伐高丽,认为“以舟师自东莱帆海趋平壤,固易”,“于是北输粟营州,东储粟古大人城”进行战争准备。大人城作为海军补给地再次浮出水面。贞观十七年,唐太宗令太仆少卿萧锐于河南道诸州转粮入海。次年,锐奏称:“海中古大人城,西去黄县二十三里,北至高丽四百七十里,地多甜水,山岛相连,贮纳军粮,此为尤便。”《唐会要》卷九五《高句丽》载:“张亮水军七万人”,其中“劲卒四万,战船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
《永乐大典》中的《漕运水程》记载了元代多条自南向北的漕运路线:其中一条至成山后“一日夜至刘岛,又一日夜至芝罘岛;再一日夜至沙门岛;守得东南便风,可放莱州大洋”,另一条“过成山北面一带并芝罘岛、登州一路木极岛等处,近沙门岛山,或铁山嘴开放莱州大洋”。“上项所由,各险恶去处,设遇风涛不甚猛恶,可以预为转调躲闪,或收入山岛藏避,守伺风平浪,然后行使。”芝罘岛恰恰属于有山岛藏避的避风港;而“滩浅狭洪沙硬,湖汛长落不常,但遇东南风,本处船聚稠密,则有妨碍之虞”,黄河营就是此种状况,并不适合避风补给。
《福山志稿》称:清初期之前,“元明海运之道,皆泊芝罘岛,而烟台无闻也”。历代芝罘岛海口均在芝罘岛西侧的黄海芝罘口,清时,芝罘口也属于“冲汛”之口,即“往来必经驻泊定程者”,航运上的重要性仍然大大高于渤海内湾的黄河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汽船驶入,避风要求降低,才改为岛东侧烟台湾。
《黄县志》又记载:“(大入)城上有海渎祠”,并注释:《元和志》《寰宇记》并云“海渎祠在大入城上”,县、府《旧志》俱失载。唐朝形成了以“四渎”“四海”为中心的水神崇拜,对“四渎”“四海”的祭祀礼制进一步提高,海、渎相继被加封为王、公。唐玄宗天宝十年(751)正月,以东海为广德王,南海为广利王,西海为广润王,北海为广泽王,分别按春、夏、秋、冬四季祭祀,并有定制:“岳镇、海渎祭于其庙,无庙则为之坛于坎。广一丈,四向为陛者,海渎之坛也。”唐代的海渎祠也很可能就在芝罘岛上,到宋代,才迁徙至现在的莱州东海神庙。(刘建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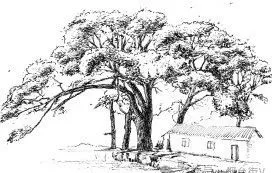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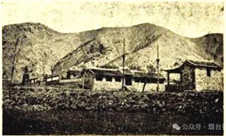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