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端午,堂弟总会从百里外的老家给我送来他亲自包好的粽子。屈指一算,他给我家送粽子这个习惯坚持了快四十年了。
上世纪80年代,交通尚不发达。每年端午节前,堂弟就坐客车来给我们送粽子。每次我去车站接他,堂弟在车站把粽子交给我后,怕坐不上返程客车,歇都不肯歇,直接坐原来这趟车返回。我见如此麻烦,不知劝他多少回别来送粽子了,但每次堂弟都是憨厚地笑着说:“俺大(爸)说了,俺大大(伯伯)喜欢吃老家粽子的味道。”
虽然我吃过各种不同口味的肉粽、豆沙粽、赤豆粽,有荤有素,咸甜兼备,但我还是对故乡的桲椤叶包的粽子情有独钟。

记得在老家的时候,每年临近端午节,母亲会早早去集市买来桲椤叶,在水里泡上几日后再包粽子。这种桲椤叶的形状跟人的手掌差不多,但比手掌要大上几圈。这种叶子包出的粽子有一种独特的香味。粽子用桲椤叶包裹上糯米,包成长方形,对叠着用稻草绳子捆绑起来,一个粽子有30多厘米长,15厘米宽,六七两,饭量小的吃一半就饱了。
据说在孟良崮战役中,我们村里为了支援我军将士,包了许多这种像鞋底般大小的粽子给战士们吃。看来,桲椤叶粽子也为这场战争的胜利贡献了一份力量。
母亲把包好的粽子放在一个大黑瓷盆里,上面放上箅子,摞上重物,把粽子里的水分挤出来,压实后,再上锅煮。一铁锅粽子不算准备料,光包粽子常常就需要一天的工夫。
煮粽子的灶下要烧在山上长的松树枝,那样粽子才入味。先是大火煮上几十分钟,然后用小火慢煮。当粽子出锅的时候,粽子糯米味混合着桲椤叶的甘甜清香味道扑面而来。
凉透的粽子外表不怎么美观,给人感觉还有点粗糙,但剥开桲椤叶,里面黏稠的糯米颗颗饱满,那味道无与伦比。在我心里,那真是人间美味。听村里老人们讲,新中国成立以后,好多老战士回访这片土地时,都表示想再品尝一下桲椤叶包的粽子。
上世纪70年代,农村日子过得比较艰辛。那时每到端午节,早上,母亲给我和姐姐一人准备半个桲椤叶包的粽子。我常常急不可耐,三口两口吞进肚子里,跟猪八戒吃仙人果似的,还没品尝滋味,就没了。眼睛就盯着姐姐那份,姐姐就把她那份又让给了我。
其实,每年来送粽子的堂弟,跟我们家半点血缘关系也没有,只是同村的人。我们两家的交往还得从父辈那代说起。上世纪50年代,我老父亲在几十里外的金矿上班。有一次,他去市里的军队医院办事,恰巧碰到我这个堂弟的母亲在医院走廊上徘徊。好心的父亲上前询问,才得知是堂弟父亲患了肝炎住了院。医生让多吃营养补品,那时候日子艰难,叔想吃鸡蛋,但婶婶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了,正为这事难过。父亲听后,二话没讲,去给叔叔买来了鸡蛋,还把他当月开的8元工资都给了婶婶,让她给叔叔买点营养品补补。叔叔住院的三个多月里,父亲经常买营养品给送来,叔叔一家人感动地说,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叔治好了病回到村里,我们两家就开始常走动。叔只要家里有点好吃的东西,准会送到我家里。我父亲只要回家,叔就把父亲叫到他家里吃饭聊天,把我父亲当成亲哥哥。
叔有个祖传手艺,就是包粽子特别拿手。他知道我父亲爱吃粽子,每年端午,他都亲手包好粽子,让婶婶给我们家送来,年年如此。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全家跟随父亲“农转非”到了城里,两家人并没有因为距离远了而关系断了。开始是每年端午,叔坐车来给我们送粽子。后来他患病行动不便,就让堂弟替他来送,一年一年从未间断。
时光荏苒,叔和我父亲相继离开了这个世界。每年端午,堂弟还是把在家包好的桲椤叶粽子送来。
如今逢年过节时,堂弟一家会开车到城里跟我们相聚;我们休息的时候也会回村里到堂弟家住上几日,那感情比亲兄弟还亲。
今年端午节前,我带着老婆孩子回到堂弟家,堂弟和弟媳忙活着包了好多粽子。浓浓的桲椤叶粽子的香味溢满农家小院,诉说着久远的情怀。(李启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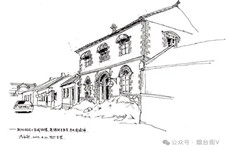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