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在年的门槛边,耳旁忽闻“糖瓜”“冰糖葫芦”……一声声叫卖此起彼伏。那富有穿透力的诱惑,引得一群垂涎的孩子们跟在卖货人的车后追赶。孩提时的年,就是在这些叫卖声中拉开序幕的。
上世纪70年代末,我村曾在烟台城里做过糖坊生意的孙振萼大爷,与生产队的老少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开糖坊。大爷已丢下近三十年的制糖手艺,终于在有生之年又有机会大显身手了。
糖坊坐落在村西,宽大的院子中,架着八口十印大锅。走进院子里,永远都是弥漫着热气与烟气,氤氲缭绕。糖坊主要加工的产品是糖稀,为各糕点加工厂提供原材料。
糖稀如何熬制,让我心中生奇。为了寻找答案,我寻访了大爷的长子,当年与大爷共同打拼,如今已八十有三的孙世逊大哥,请他做了初步的概述。
做糖稀前,首先要用大麦或小麦,在泥盆里生芽,一般芽长至一厘米为宜。这边麦芽长着,那边制作糖稀的工序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将选好的玉米颗粒,在粉碎机上粉成2.5毫米左右的玉米 ,按25公斤为一锅的量倒进锅里,加适量的水,慢火熬粥。熬至玉米 完全熟透,用手捻一下里面没有生 ,再将生好的麦芽粉碎,按十比一的比例加入锅中,搅拌均匀。为何要用麦芽呢?因为麦芽起着稀释、分解、沉淀的作用。有了它,能使一锅稠稠的粥,慢慢地变成上面是清清的水,下面是沉淀的渣。即使如此,仍需滤渣。糖坊有一大缸,在它靠下的部位安有一个水龙头,用来放过滤后的原液。在缸的上口,铺一蒸锅用的软箅帘作为过滤网,然后将锅里所有的汁渣依次盛起,倒入箅帘上进行过滤。滤后留在箅帘上的渣,可以用于喂猪。沥进缸里的汁液,就成了做糖稀用的原液。
将原液从缸里放出来,再倒进锅里烧,边烧边用铲子(梧桐木制作的)在锅底及锅边来回铲。这一工序,为的是不让它糊锅。用苏棍(梧桐棍)挑糖稀,看拉丝的程度。如果拉不出丝,或拉出的丝少而短,需继续加柴熬制。若挑起的糖稀能拉出四至六根长丝,这锅糖稀的熬制就算成功了。最后将熬制好的糖稀,装入大铁桶内封好,它的制作流程就此完成。
此时,一桶桶糖稀如同一群十七八岁丰盈待嫁的“公主”,可谓炙手可热。你看吧,来“接亲”的车辆,可以用浩浩荡荡来形容,排出去老远。其中有自行车、小推车、拖拉机、大解放……它们“嫁”的“婆家”分别在解甲庄、初家、埠岚、七夼、福山、西南村,以及乳山、文登等地。
特别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前和临近过年时,糖稀更是供不应求。大大小小的客户,天不亮就赶来排号。做好的糖稀来不及凉透,一装进铁桶,立马被抢走。天渐渐黑了下来,还有没买到的客户。大爷不忍心看着大老远奔来的客户空手而归,便与大商家协商,匀出一点给那些小客户,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大爷的举动,赢得了客商们的钦佩与赞许。
当然了,那些制糖人也是昼夜轮班,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挥汗如雨地守候在熬糖的热锅旁。
烟台“北来香”副食品加工厂为了抢占市场,满足供应,主动为糖坊提供玉米、大麦等所需的原材料,并送货上门。同时也将自产的各种点心带进我们村,开设了“北来香”连锁店。那些琳琅满目的食品,不仅花样玲珑精巧,而且口感香甜适宜爽口,令人称赞,更有亲民的价格。一时间,“北来香”如同落在俺村的一只金凤凰,引来八方客,让乡下人算是开了眼。村民们每天如着了魔似的,心里有了放不下的牵挂,有事没事总去“北来香”转转。
进了腊月,糖坊不仅要加班加点儿,还需增加人手,做小孩子喜欢吃、小年供奉灶王爷的糖瓜。

资料图 文图无关
做糖瓜所用的糖稀要盛在泥盆里,因为泥盆的吸水性强。使用前,先将泥盆在水中浸透,这样能使盛在盆里的糖稀不易粘到盆边上,解决了无法清除的麻烦。糖稀凉了还会变硬,为了保持糖稀的温度及柔软度,需将盆放到热乎乎的炕上。
一切准备就绪,糖瓜制作便开始了。做糖瓜的师傅用双手从盆里捧出适量的糖稀,像做拉面似的,两手轻轻地将糖稀抻长,再叠起。经过多次的反复拉长、叠起,手中的糖稀变得松软、暄腾。此时,再将它套在锅边镶嵌的拐子上,徐徐拉抻到一定程度后,另一人迅速将拐子上的一头拿下,两人扯着,轻轻将两片糖料的边缘粘在一起,形成中间空心状的糖条。趁着它还柔软,由专人勒线。勒线是将这一糖条按基本相同的间距,勒成一个个矮矮胖胖的糖块,如一堆小弥勒。这些小精灵的诞生,便是令我们垂涎的糖瓜。为了不使糖瓜粘连,当时的做法是摆一层糖瓜撒上一层粉。
糖瓜做好后,论斤批发。有代销点来进货的,也有个人批发回去卖的。一公斤糖瓜批发价四元钱,一公斤能称近二百个。算起来,一个糖瓜卖家需要二分多的本钱,能卖五分钱,赶上不好卖时,略小一点的四分、三分也卖。一天下来,比在生产队挣工分要翻上一倍还多。一些中学生得知后也觉得眼红,到了放寒假时,纷纷去批发糖瓜,沿村叫卖。如果探听到哪个村庄放电影或演节目,傍晚时,不管天冷路滑,早早就到了场地,几声“糖瓜”的叫喊声,便引来一些馋嘴孩子的围观。
傍年根儿,糖瓜生意尤为火爆。人人都想借此多抢点货,多挣点钱,但是做糖瓜的师傅们使尽了全身解数,也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为了让大伙都能拿上货,大爷提出了人均定量批发的规矩,避免了为此打破头的局面。
糖坊火爆的生意持续了二十多年,后来,随着副食品行业的飞速发展,很快跌进了无人问津的谷底,成了一代人的记忆。(孙玉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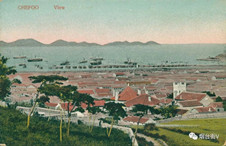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
鲁公网安备37061302000010号